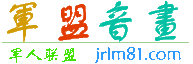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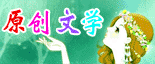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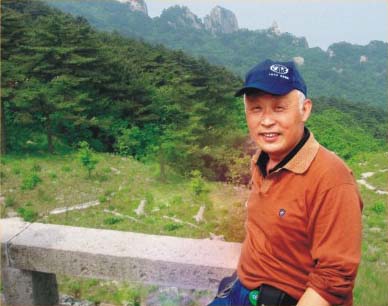 |
长篇传记——漫漫人生 作者:高天 |
第二十九回大精简殊途遇知音
学二胡寻觅新人生一九六二年以后,精简下放之风逐渐吹遍了松兹县每一个角落,一时间,县以下各行各业都在裁减工作人员。人们无不时刻担心,啥时候会轮到自己头上。
自收费员小项、师兄弟谭炎亮被首批精简走后,医院除了我一个年轻人外,再没有第二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了。所以,我一直在沉默寡言中过日子。一天,医院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中等个头、五官端正,端庄而不失俊俏,大方却又显稳重。白里透红的皮肤镶嵌出天然的柔滑,黑白明亮的双眸勾勒得妩媚动人。尤其是六十年代受电影《柳堡的故事》影响,城乡最时髦风行的黒亮过臀的长辩,随着轻盈的步伐,来回不停地在臀后左右甩动,着实让医院的医护人员无不流露出惊羡的目光,情不自禁地发出“啧啧”的赞美声!她,就是医院护士余大姐的妹妹—秀珍。
秀珍她是乡村小学的一名老师,本当青春豆蔻年华,正待一展人生风采,却偏偏赶上了国家精简职工的年代,被首批宣布精简回乡。秀珍自幼父母早逝,从小离家外出,颠沛流离,靠姐姐拉扯长大。好不容易熬到中学毕业,谋上了一份农村小学教师的工作,却又中途失业无家可归,只好到城边唯一的亲人姐姐家暂且寄居。
秀珍的姐姐前夫被打右派后病逝,一个女人拖着几个小孩生活的确艰难,后来又找了一名邮政职工,本想粗茶淡饭把孩子们拉扯大,岂料穷人的盐罐偏生蛆,丈夫也被首批精简回到家乡农村。在大队当一名会计。后来接二连三地又生了一男一女,全家七口五个小孩,医院总共才半间住房,因而无法容纳妹妹。秀珍最终碾转找到医院附近一个学生家里暂住,总算是安顿了下来。
秀珍姐她大我几岁,平日里,她给姐姐带带小孩、烧烧饭,有时也帮忙打打针、换换药,闲下来,就喜欢同我聊天。可能是我们年龄相仿,阅历相当,能相互倾诉心声;也可能是我们两人自幼都经历过艰难曲折,深知人世间冷暖苦楚;更可能是,在那种特定时代背景下离校门参加工作又遭受精简下放的不幸,使我们一见面就能萌发出一种心心相惜的同情感,产生出一种殊途结知音的人生共同语言,所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自后我们一直以姐弟相处。从童年苦难的岁月到少年成长的艰辛;从各自经历的甜酸苦辣到刻意追求美好生活的磨练;从个人的爱好到未来的理想,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渐渐地,十四、五岁的我对秀珍姐既崇拜、敬仰、又憐惜有加,年大的秀珍姐对我既关心、爱护、又备至有甚。频繁亲密的接触和年龄、处境的差别,曾受到旁人的议论和父亲的干预,但纯真的朦胧情谊,割不断相互交往和关心。我们两人经常一块吹口琴、唱歌,学作诗、下棋、谈心。姐姐热爱弟弟的热情、天真、开朗和诚实。弟弟崇尚姐姐的成熟、稳重、多才和善解人意。我从秀珍姐那里学会了待人接物,为人处事,增添了宝贵的社会知识和财富;姐姐从我身上得到了宽慰、喜悦和开心,减除了精简失业带来的烦恼、孤独与苦闷。
那时,电影明星风靡一时,王心刚、赵丹、张瑞芳、田华、王晓棠、秦怡等著名影星的巨幅画像挂满了县城影院。因而看电影,特别是看明星的电影,成了人们主要的精神寄托和最大的爱好。
五里墩距县城只有五六华里,走小路罗家湾、雷公岭、小街口一插,步行约半个多小时,更是路近方便。为解姐姐的烦闷,我们时常相邀进城看电影。只要是晴天,公社社直单位的男男女女,对看电影都兴致特高,几乎每个星期都互相邀约进城看电影,有的骑车、相互带着,有的步行,回来时,大家一路谈笑风生,好不热闹。在这些电影迷的大军中间,每每都少不了我两人。医院的一辆弃用的旧自行车,我拿到街上请人修了修,就基本上成了我们看电影的御用工具。只要是逢明星主演的新电影,我们总要先睹为快。不是提前排队购票,就是找关系托人买票,真是场场不脱穆桂英。
六十年代初期,老一辈影星主演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冰山上的来客》、《秘密图纸》、《国庆十点钟》、《英雄虎胆》、《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的确使老百姓是百看不厌。特别是后期新一代影星,如张瑜主演的《知音》、《廬山恋》,刘晓庆主演的《小花》,祝希娟主演的《红色娘子军》,祝新运演的《闪闪红心》等影片,更是场场爆满,成为男女老少、街头巷尾、茶余饭后议论不休的主题。最使我难忘的是,《红楼梦》电影刚一首映,电影院的工作人员简直是红得发紫,没有关系,真是一票难求。一部片子放下来要三个多小时,头几场影票,各大小领导都近水楼台拿走好票。小百姓找熟人开后门,也只是瞎子打拳四路无门。无奈我只得求爷爷、告奶奶托人买了两张子夜后十二点第三场的影票,我同秀珍姐和社直单位的同伴们看完电影从城里出发己是三点多钟了。一开始,同行的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我骑车带着秀珍姐也轻松自如,一路顺风。后来由于自行车骑的太苦,链条老是脱落,我一会上、一会下,老是常下车挂链条。渐渐掉队后人都走尽了,没法子只有上坡就下来,下坡就顺势趟上一段路。这样走走骑骑,过了雷公岭,到了罗家湾小路时,我让秀珍姐先坐好,又准备顺下坡趟上一段路,那知不小心沙石路削了撇,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了路旁的水稻田里,我赶紧把秀珍姐拉起来,两人相互对望着浑身、满脸的泥水,弄湿的衣服,不由得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自行车再也推不动了,好在离罗家湾秀珍姐寄住的炳火家不远了,我扛起自行车,秀珍姐帮忙扶着,好不容易来到炳火家。我洗洗干净,把车丢下、就往回赶,到医院时,天快要亮了。
朦胧的情感,纯洁的友谊,真诚的交往。是那种特定年代,同龄人最有代表性、最真实的友谊象征。
那是一个秋日的清晨,我晨练未回,秀珍姐她不打招呼就静悄悄地走了。由于她无家可归,被县劳动局重新安排到财政局搞农税助征员。临走,她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后来,才知道她被重新安排了工作。我专门进城去找了她几次,但她已被派往很远的乡下收农业税去了。那时的财政局就在我家对面,我时常傍晚回家,就在大门口徘徊,希望能碰见上她,有时我还坐在大门口石狮子上吹着口琴,盼望姐姐能听到熟悉琴声会出来见上一面。可她就是一直未回城。我也不好到单位去打听,从此,就渐渐失去了音讯。
一九六三年仲夏,恶运也最终降到了我的头上。我被公社最后一批宣布精减下放。结束了三年的中医学徒生涯,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步入社会后的人生第一站,告别了共亊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师辈和同仁,象茫茫大海的一叶扁舟,半途而废地再次去寻找新的人生航程。
我被精减回到县城家中之后,到县劳动局报了个到,等待着重新安置。然后,就整天窝在家里闷闷不乐,无人交谈、更无人解闷。闲下无亊,我就四处借来许多古典章回小说整日闷头在家里看,看累了,就蒙头大睡。晚上才懒洋洋地到城里大街小巷瞎遛达。一次,转到县文化馆附近,老远就被一阵阵悠扬悦耳的琴声所吸引,我寻琴声渐渐来到近前,原来这优雅的二胡声,是从文化馆一个窗户里传出来的。从灯光映在窗户上的人影看,是一个中年男子〔后来才知道是王馆长〕正在全神贯注的拉一首非常动听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我伏在屋外的窗台上听了一遍又一遍,真是听上了瘾。不觉渴、不觉累,也不怕蚊虫叮咬,一站就是两个来小时,两腿渐渐发麻了也舍不得走。直到人家关灯休息了,这才依依难舍地离开。
第二天,我心血来潮,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百货公司买了一把几十块钱的好二胡,又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二胡演奏法》的书,自学了起来。开始,我从最简单的《东方红》、《孟姜女》和电影《闪闪红星》中的《我们都是共产主义儿童团》曲调学拉起。起初,用弓拉琴弦,就象是拉锯一样生怕用少了劲不响,结果是难听异常,象老鸭公觅食一样非常割耳。我怕人笑话,渐渐找出了用铅笔做琴码的巧门,声音既小、又清晰。按照教材,我先从一把的〔1·5〕弦学拉起,慢慢地学〔5·2〕弦,再接着练二把,练上滑音、下滑音、颤音、揉弦、连弓、长弓、抖弓、快弓等,一个夏天下来,我的二胡也自学得有模有样,拉起简单的曲调来,也是有板有眼,不再象鸭公叫了。后来,我慢慢结识了王馆长,陈家瑞、蔡中兴等文艺界的专业老师,琴技才有了很大的长进。在原有基础上我又学拉6·3弦、2·6弦、3·7弦,并能下滑拉二把、三把。一般的独奏曲如阿炳的《二泉映月》、刘天华的《病中吟》、还有《江河水》、《光明行》、《赛马》等独奏曲都能略知一二,凑合着学拉几段。
人生的道路说起来就是那么离奇古怪,我被精简下放在家待业整整三个月,既未见到秀珍姐,也无人谈心解闷,在闲得无聊的度日如年中。却也因祸得福,饱览了许多古典小说、名著,还学会了拉二胡。这为日后的漫漫人生路上发挥个人特长,参与朋友交往,参加文艺创作、演出活动增添了无尽的乐趣和时光色彩!同时,又意想不到的是,不出几天我也被重新安排到县财政局工作,真正与秀珍姐成了殊途同归的好朋友。真乃是:漫漫人生修远兮,坎坷路上初相识,只因精简才分别,岂料殊途同归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