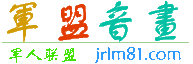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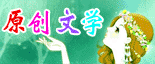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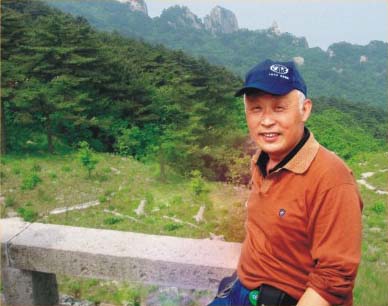 |
长篇传记——漫漫人生 作者:高天 |
第十四回
送妇孺勇显侠义胆
破窗塞急智搬救兵县城西北面约六华里的的马安山,有一叫跑马场的小煤矿。因离城很近,是当年县直机关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点。反右斗争后期,一些所谓问题较小的人,统统安排在这里劳动改造思想。一个炎热的傍晚,我吃过晚饭,正和弟弟们在昏黄的电灯下做作业。突然,只听隔壁方家屋厅堂里有人在哭,全屋的人都闻声前去看究竟。原是租住美玉姨家房子的雪枝姨一边哭一边说:“现将哟呵好呀!孩子他爹在煤矿里摔伤了,天漆黒我一个家里人,孩子又小将哟呵去哟!”我母亲和美玉姨都劝她不要急,把孩子留下来大家照顾。但孩子小,不足两岁,又常要喝奶,留在家里也不行。此时,左右隔壁邻居中都没有大男人在家,女的夜晚又走不开,一个妇道人家去,天黒路远,还背着一个小孩,况且当时又正盛传马头狼四处出没伤人,千万不行!正在大家为难之际,我自告奋勇地上前说:“我驮小孩送雪枝姨去!”在场的人都看着我说:“你能行吗?”我拍拍胸脯说:“放心吧!我有的是力气,驮个小孩还不行!”母亲信任地看着我点了点头,马上坚定地对雪枝阿姨说:“行!就让学佬陪着你去吧,路上带个手电筒,还要带一根木棍,一来探路拨拨草,二来若真有马头狼好防身。”我为了防蛇虫蚂蚁叮咬和茅草荆棘刺划伤,随即穿上长脚裤和解放鞋,并扎紧裤脚、腰带,用布背篼背上小孩,手里提根幼小常练功用的齐眉棍,伴着雪枝阿姨一起上路。
我们一行两个小孩一个大人,出方家屋沿北门街向北门城外走去。这时,只见街道两旁冷冷清清,从门窗里时隐时现透露出些昏暗的灯光,本来夏日炎炎的晚上,平日里街头休息纳凉的人很多,只因近期传说马头狼出没伤人闹得沸沸扬扬。所以,若大个县城,一到傍晚,家家关门闭户不敢出入。
出了方家屋,来到县总工会门口,只见门前一对阴森森的石狮子,瞪着两只铜铃般的大眼睛,望着我们一大两小一行漆黑的夜晚反往城外而奔的不速之客,仿佛感到很是奇怪。走近曹家香店,对面就是好友国翰家,我本想喊上他一块去,路上好有个壮胆说话的人,岂知喊了几遍,国翰就是不敢出门。我心想,你个胆小鬼,离了你张屠夫还真吃混毛猪不成。于是,一边迈开脚下的步子,一边默数着街两边的人家往北门城外走去。国翰家对面是桂荫斋、金家祠堂、接着是荷香姨家,再过去是石求旺、石求林、张志府、曹老三、锅铁厂、柴家饭店、张裁缝、熊家祠堂、火记、葆华、济汉、世洪、巧枝、泽润、汉卿、泗玉、金枝、的熖、大熖、旺生、瘦子、林生、九龄、朱大、祥元、洪涛、育成、天赐、五英等人家。我们走过五英姨门口,隔菜园远望着我们弟兄曾经蒙受姑祖母福荫庇护的《如意庵》和从大佛殿门里透出的微弱烛光,以及晚风送来的阵阵清香,想着姑祖母昔日的关爱和教诲,顿感浑身胆气横生,充满力量。我把背驮的小弟弟往上一起,嘴里喊声:“雪姨,快到城门口了,咱们快点走!”说着便迈开大步加快了速度,不一会我们一行到了城门口。稍稍歇息一下后,马上又赶往城外。
出得城来,过了护城河,放眼望去,顿觉四周冷风飕飕,一片荒凉。右边是曾经枪毙过人的荒树林,左边是掩埋夭折小孩的乱坟岗。白日里野狗撕咬的烂布、破片,一派狼藉,行人白天尚不敢近前目睹,此时漆黑的夜晚更是令人毛骨悚然。雪枝阿姨紧张得哆嗦着往我身边紧靠,手里的电筒不停地朝四周乱晃。我提棍的右手虽然也紧握得直冒冷汗,但嘴里还象个大男子汉一样,装模作样地安慰雪枝姨说:“别怕!别怕!有我那。”其实讲话的声音也是颤抖不停。只是雪枝阿姨自顾不暇,听不出语气来罢了。我们提心吊胆地走了百把米,来到父亲的同亊刘老医生家门前,这才松了一口气。再往前走,左手是北关队的田畈,右边是苗圃。过了一座废砖瓦窑,就到了大觉寺。走过大觉寺,再绕过宛家塘东北角就到了出城后的第一个大屋场—郑家园坝。从郑家园坝到跑马场煤矿,走小路没有屋场和人家,尽是茅草丛生的田坝小路和一人多高芭茅的荒山岗,但路近只有三华里地;走大路要从东山嘴绕,路虽好走,路程要远一倍。这时,我望望悬挂天边镰刀样的毛毛细月才刚爬上东山,远望大地蒙蒙胧胧不太显亮,近看小路还依稀可辨。于是说:“雪枝姨,我们还是走小路吧,这样能早一点到。”雪枝姨走过近前摸摸看看我背上的孩子说:“学佬奀,你也背了好大一会了,还是歇歇换我来背一会吧。”我说:“不累,我再背一段路吧。”雪姨说:“前面路小,你眼睛看得清楚些,就在前面探路吧。”说着解下孩子背到自己背上。这样,我们大小一行三人沿着茅草丛生的田埂小路向前慢慢摸去。
我右手提着齐眉棍,左手打着电筒,象孙悟空陪师傅唐僧西天取经一样,在前面开起路来。一路上,我瞪大眼睛左右观察,侧耳听声四周搜索,此刻我担心的不是怕传说中的鬼怪,从心里头压根儿也不相信世上有鬼,而是担心真碰到马头狼就麻烦了。我小心翼翼地在前面领着路,雪枝姨背着小孩在后面紧紧跟着,茅草过膝的田埂小路,高一脚、低一脚非常难走。一不小心,在过田埂放水缺口时,雪枝姨右脚滑到稻田里,扑通一声水响,哎哟一声,双膝跪倒在田埂上,背上的孩子也吓得大声哭了起来。我吓了一跳,赶紧返身来扶,幸亏雪枝姨眼急手快,双手赶紧抓住了田埂边上的茅草,才未跌倒,也未摔着背上的小孩。我连忙拉起雪姨,抱过孩子背在自己身上。走过一片稻田,远远望见前面燐光闪烁,我心想,这里方圆几里都没有人家,哪来的灯光?正在怀疑,突然前方又闪了两下。“不好!有狼来了!”我马上大喊一声:“雪姨注意!赶快把电筒直射前方光闪处不要灭。”这时我拉紧背带绳,紧紧腰带,双脚扎好马步,两手紧握齐眉棍,憋住呼吸,目视正前方,拭目以待。一分钟、两分钟尚无动静,约十分钟过去了,仍无动静。这时,雪姨紧靠在我身后,用电筒直射着前方低声结巴着说:“光不闪了,会是、是、是马头狼吗?”我镇定地说;“雪姨,你把孩子解开背过去,把电筒给我,我上前去看看。”我左手打着电筒,右手提着齐眉棍一步、两步,缓慢向前探去……。大约接近光闪处时,只见是坟地周边翻露出的许多白骨,根本不见狼的影子。我这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满头的大汗,顿时变得冰凉!直往背脊沟里渗透。我回过头大声喊着:“雪姨,别怕!不是马头狼,是坟地的燐火。”我返身来拉着雪姨爬上了前面小土岗,只见一社寺庙也就在跟前,庙里的灯火也在一闪一闪跳跃着。我和雪姨象大海行船望见彼岸一般地兴奋得赶上前去,瘫坐在社寺庙门前的草地上。
过了社寺庙、绕过一塘坝,就望见了到了马安山屋场的灯光,此刻,我心里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因为,再翻过马安山屋场的小山包,就能看见煤矿了。雪姨这时心里也甭提有多兴奋,仿佛忘记了是去看受伤的丈夫,边走还边哼起了黄梅小调,背上的小宝宝也觉得安全了,呼呼睡得正香。
煤矿,终于在我和雪姨大小三人的担惊受怕、奋力跋涉和热切期盼中到达了。雪姨的丈夫其实没什么大碍,只是摔伤了腿,骨头断了。接到妻子和儿子的星夜来探,真是高兴无比。同亊及矿友们更是热情地倒水、端茶、打饭,忙得不亦乐乎。大家看着墙上的挂钟己指向深夜十一点,听着雪姨诉说一路上的经过,不约而同地把赞赏的目光一齐投向了我。一个个都称赞我人小、胆大、心善、象老子一样有侠肝义胆。我听着脸象大姑娘一样涨得通红。这时,全县年龄最小就被打成右派的汪三哥,端着两大碗热气腾腾的饭菜进来说:“我这个小老弟别看年纪小,可是武术世家出身,自幼跟随父亲—松兹县有名的妙佬师父学武,功底可是不差。你们看,只要用手一摸这两头包铁、中间滑亮的木棍,就知是经常习武之人。”我也真的饿极了,大口扒着碗里的饭菜,任随三哥去吓吹。饭后,张叔叔硬要把两毛钱塞给我,说是给我买点东西吃,我说什么也不收。当晚,我就和三哥插伙睡了一晚上。
东方天刚放亮,我赶紧起床,擦把冷水脸,提着齐眉棍就往家里赶,要抢时间赶回城里去上学。迎着满天的朝霞,向着旭日喷薄欲出的东方,我迈步走在清晨田野的小路上。一路上,我拼命地吮吸着旷野的新鲜空气,随着轻盈的步伐我放声高歌,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因为,我终于象小说里的勇士一样黒夜送妇孺,做了一件助人为乐的好亊。
又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和令志、铁牛、国翰等几个小伙伴们相邀去掏红芋。我们挎着竹篮,拿着小扒儿,一同往城西三华里地的东山嘴跑。平日里只要到午、秋收季节,我们几个小伙伴都相邀到东山嘴拾稻子、捡麦穗。这里田地多、离城又近。我们来到己挖过红芋的地里,大家掏呀掏了半下午,就是掏不到一个遗漏下的红芋。每人篮里除了几根红芋根和破红芋外,确实收获太少。铁牛骂着说:“这些该死的,挖得太干净了!”令志也跟着骂“这些死鬼,怎么也不留点小爷爷吃吃!”我说:“别骂了,骂也骂不出红芋来,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们几个走到官厅屋后面,看见有几个妇女在偷挖队上的红芋,铁牛、令志也赶忙跑过去挖,我还未走到地头,生产队看禁的人就来了,大人们都飞快地跑了,几个小孩倒霉被抓住了,看禁人不分青红皂白把我们连人带篮子统统关到队里仓屋里。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又渴又饿,队上还不见来人问亊。这时,我气不打一处出,本来自已未偷红芋,你不问三七二十一把人给关了不管。我们几个一望墙上窗户几根快要腐蚀的窗塞,实在憋不住,大家就喊着“一、二、三”使劲拉断了一根木窗塞,然后又把小个子铁牛给塞挤出去,让他快去搬救兵。一会儿,队上看禁来人了,看见窗塞断了,小孩也跑了一个,更是大发雷霆。我上前跟他论理说:“捉贼捉脏,我们又未偷红芋,凭什么乱关我们?”令志更是拿出耍赖的本领,在地上又哭、又滚,国翰也装起肚子痛来。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时,队长来了,被这乱七八糟的场面吓住了,命赶快放人。这时救兵也到了,令志母亲是出了名的难缠户,来了后又泼又骂:“你们欺负我孤儿寡母,没偷红芋硬赖人,还乱关人。共产党的天下还有没有王法?走!我们到公社讲理去。”队长连忙说:“我们错了,不该关小孩,对不住了。”令志哭着说:“篮子全被你们踩坏了,赔我的篮子”队长赶快让人把篮子拿来修修整整,又一人给装了一篮红芋,这才算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