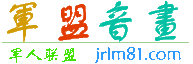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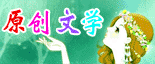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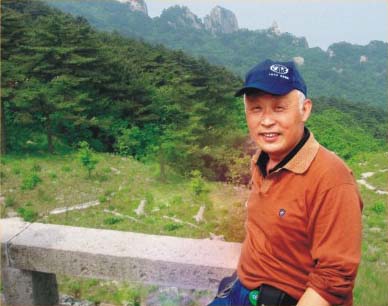 |
长篇传记——漫漫人生 作者:高天 |
第十三回
定无罪父亲被释放
开荒地瓜菜渡灾年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在饥饿线上艰难渡日的我一家,一大早起来,只听得屋后院的柿枣树上喜鹊在“吱吱嘎、吱吱嘎“地叫个不停。三弟说:“喜鹊叫,喜亊到,八成今天又是食堂有肉吃了吧。”果不然,我弟兄三人一放学回家,真是天大的喜亊降临了,只见父亲笑嘻嘻地在家里端坐着,我们弟兄一下愣住了,然后,一拥而上,抱着久别的父亲大哭了起来。原来父亲被蒙冤关押了十一个月后,刚被无罪释放回家。父亲明显瘦多了,他那白净瘦削的脸上虽然难见一点血色,但精神还是很好。可见他在狱中尽管吃了不少苦头,由于心胸开朗,身体尚无大碍。只见一纸公安局写给城关大公社的便函上写着“高某某现无罪释放,由你社安排。”几个简单大字。显然,这是一纸不负责任,含糊不清的文书。既说无罪,为何被无辜关押十一个月之久?既然无罪释放,为何又不提恢复职务、工作及补偿工资损失?由你社安排,到底是安排在何处、何亊?这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专政年代,问谁、谁也说不清楚。这种亊实如非的结论,无疑给日后我们弟兄四人的成长、进步,留下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好在全家都沉浸在重逢的喜悦之中,无心去思考这日后的发展和牵连影响。
一开始,可能是由于那概念不清的文书原因,公社没有安排父亲回城关医院上班,更无从谈起职务的恢复和补偿经济损失,而是安排父亲到城西大队王屋当住点医生。后又安排到离县城三四华里的弹山大队高家大屋,一个救治浮肿病人的临时医疗点上当医生。当时,饱受饥饿的群众,绝大多数骨瘦如柴,营养不良。国家下拨了大量的专项资金,救治从三年自然灾害饥饿的死亡线留下的体弱多病的社员群众。并专门下发了用黄豆和玉米磨制成了一种营养粉,每天每个病人发六两,严重病员还发一些奶粉和白糖,让他们迅速恢复健康。那时农村医生特少,病人又太多,临时点上收治了几十个病员,而只有父亲一个医生。于是。父亲就找大队要了几个既年青、又懂点医务的村医,帮忙搞护理,这才得以正常开展救治工作。起初,父亲很少回家,后来病人渐渐稳定了,就星期六傍晚回来一趟,第二天天不亮就赶回去。母亲为了尽快恢复父亲的身子,总是省着把每天从食堂打回来的饭,扣下一勺,积存到星期六晚上就夠有一碗饭,热给父亲吃。可父亲每次看看身旁几个饥瘦的孩子们,说什么也舍不得吃。这样,母亲有时只好等到孩子们都睡觉了,再热给父亲吃。
党的庐山会议以后,由于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们仗义执言和积极争取,全国适时地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普遍撤散了大食堂,允许社员搞自留地,部份放开了农产品市场。这给灾难的神州大地及时注入了新的生机,频临饥饿潦倒的松兹百姓,活受饿罪的日子总算熬出了头。寸土必争开荒地,种瓜、种菜填肚肠,一时间,松兹县掀起了自发开荒种粮、种菜的热潮。
我的父亲虽然无罪释放后仍然当医生,但由于没有真正平反落实政策,每月工资基本上只发点生活费。因而收入甚少,母亲还象以前一样帮人洗衣和做工为生,为了填饱全家人的肚子,她还总是起早摸黑地开荒地、种菜园。正上五年级的我,除了哥哥远在复兴外,兄弟中其实我就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所以,为了让弟弟们能吃饱饭,不受饿罪,更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也加入了开荒、种地、生产自救的行列。早头夜晚我放下书包就陪着母亲一道去挖地,种菜。起初,在离家较近的何家塘边上挖了两小块约六平方米的菜园,种上白菜和萝卜。后来,又在城墙坝外王鸭堰,蛮子老儿窑边上,挖了一块约十来平方的地,挿上红芋。最后,城周边的空坦被人挖光了,只好到北门城墙坝外鸭儿塘边上一个乱坟岗中间和金家塘汪家园倒塌的宅基地上去开荒。这可真是难挖得很。乱坟岗一套色的观音土,天雨烂泥巴,沾锄头无法挖;天晴铁板硬帮帮,就象小锤敲板糖,挖不动还费时、费劲。要活命,就得于,只好买来泼锄,〔山区人用来挖树根用的〕象敲板糖一样,一点一滴慢慢敲。我手上挖起了血泡,戴上手套又继续挖。有时大半天只能挖个把平方。一个暑假下来,真是愚公移山天天开荒不止,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血茧,总算挖出了分把地,当年秋季就种上了小麦。又是锄草、又是浇粪,功夫不负有心人,隔年春上竟打了近一箩小麦。汪家园更是别提有多难了。原先,这里是历史上一个大户人家的旧屋基,年久倒塌无人居住。砖头成堆、瓦片成垛、石灰渣遍地都是,锄头更是一挖一蹦。这哪是在开荒,简直是象土里淘金一样。这里真正寸土寸金,要想活命就要寸土必争。我母子俩只好先用爬梳慢慢把瓦片、石子、石灰渣一点一滴梳理筛掉,再挖一层;接着再又梳一层、理一层、筛一层,挖一层。有的还要边挖、边梳、边筛、边理,如此地蚂蚁啃骨头、时达月余,才也开垦出了不到一分地。但此处土质肥沃、不用施粪,长出来的马铃薯个头特大,又香又好吃。开荒挖地要硬功,这施肥、锄草、播种、收割,也不轻巧。好在不求产量、不交学费、边干边学。那时,我在同龄的孩子中比起来,个头算很高,力气也蛮大,但一开始,两只大粪桶就是挑不离地,后来设法在两只粪桶耳朵上再帮根短绳子,用扁担挑绳子才能挑起来。起初我只能挑两个半桶,上坡过坎还总是前后挡亊,一路泼的都是粪水,惹得总是受街坊邻居和路人的骂。后来我在上面放两片大树叶,挑的时候掌握一过平衡,就再也泼洒不了。渐渐挑习惯了,力气也大了,挑两个浅桶粪水也不费力。一次放学,我到蛮子窑边上地里去浇粪,过城墙坝爬坎时,上四十多度的斜坡,人和两只粪桶一样长,不是搁到前桶就是拖住后桶,怎么也爬不去坝上。我心想踮起脚咬着牙挺上去,前面粪桶底凑着地一碰,脚下一滑,两只粪桶全摔倒了,溅得我满身都是臭粪,好在是夏天,我哭哭擦擦眼泪、跳到何家塘里洗洗身子和衣服,又洗干净粪桶,含着泪水回家,还暪着不让母亲知道。后来,几个小伙伴晓得了,在一块玩猜谜语时,国翰说:“两个老儿一样长,日里烧火,夜里乘凉”令志说是烧柴用的铁火钳。铁牛说我出一个谜语大家猜,“三个老儿一样长,两头坐担悠悠晃,中间挑担专吃香”把挑大粪编成谜语来取笑我。大家都猜不出,还是我深有体会说:“你这家伙敢取笑我”,说着就去追打他。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弟兄几人齐心协力一起上,一到星期日或周末,大家都往菜园跑。扯草的扯草、捉虫的捉虫、摘菜的摘菜,干得热火朝天。一年下来,共开挖了七八块荒地,冬种小麦、洋芋,点蚕豆、碗豆,栽白菜、芥菜、莴笋;春点黄绿米豆、下红芋秧、插红芋,栽黄瓜、南瓜、丝瓜、茄子、辣椒、西红柿等。总之,五花八门样样都种,全家蔬菜自食有余,小麦收了几十斤、山芋挖了几百斤、黄绿米豆也共收了二三十斤,从根本上弥补了口粮的不足。从此,受饿罪的日子再也一去不复返了。那年过春节,我高兴之余,心血来潮,歪七倒八的自写了两副春联,贴到大门上。上联是:“挥锄流汗为吃饱” 下联是:“开荒种地填饥肠 ” 横批是:“自留地好”贴在厨房后门上的是:上联:“没有大粪臭” 下联:“哪来五谷香 ” 横批:“劳动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