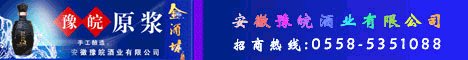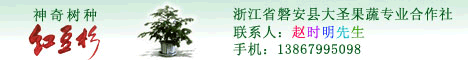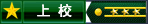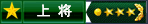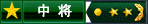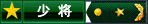有人说:父爱比山高,母恩比海深。无风无月的深夜,墨蓝的天幕上一颗暗淡的星星孤寂地挂在树梢,冷峻而肃穆。这样静的夜,给人一种恐惧,让人想到死亡即近;心情沉闷得像龟裂的土地,思绪却没有因之而枯竭,眼前忽隐忽现地飘着孩时曾经触动心灵的一幕幕,闪着曾经与母亲一起度过的短暂幸福的岁月。
记忆中的母亲已经很老了,黄褐色的脸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头发微白,往后梳着一个不大的发网。也许是我家姊妹太多、又属我最小、最聪明了,所以母亲对我特别偏爱。
记得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五姐在一起扒在桌子上做作业,那时我上三年级,虽然五姐比我大四岁,但她却才上四年级。那时我家里生活虽很拮据,但母亲还是尽力所能地让三个姐姐、一个哥哥读完了初中。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样的农村,读到初中的能有几个呢?父亲是个老实、敦厚的人,对家里的一些事不太过问,一切大大小小的负担都是母亲不分日夜地在操劳。她知道,学点文化对我们以后会有好处,无论再苦,再累母亲从不耽误我们的学习机会。只是我这个五姐,天生不喜欢学习,往学校送了多少次,任母亲苦口婆心地说了一大堆,她宁愿去挣工分,帮家里干活,也不想去学校。
最后母亲还是坚决要让她读完小学。由于这样,五姐的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好,还经常会受我与哥哥的欺负。那晚,家里其他的人都出去凉快了,只有我与五姐一块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做作业,我一会抢过她的书翻翻,一会又夺过她的本子,看看她写的不太工整的字,嘴里不住地讥笑她的笨脑瓜。我的铅笔在我洋洋自得里“啪嚓”断了,我不加思索地夺过她的笔,顺手把自己的断笔扔给了她。五姐逆来顺受惯了,拾起断笔,找出小刀慢慢地削起来。她像喃喃自语似的说着什么,我不屑,没理她。不曾想,只听“啊”的一声她捂住了手,我心里一噔,把灯顺势推了过去,微黄的灯光里,只见姐姐被划破的手指黑糊糊一片,我慌了,跑到院子大叫,“娘,五姐的手破了”!母亲应声“怎么了”慌忙走进屋来,朝身后跟着的二姐说“快找块干净的布来”!“哦”二姐应声而去。我站在角落里,怯怯地望着母亲为五姐包扎好伤口。“小妞,你愣什么还不快写作业,别耽误你学习!”“哦”我回过神来,心理稍稍松了口气。
幸好母亲没有责怪我,我心理涌起一股歉意的暖流,漫过我每一根曾经麻木的神经。母亲知道我学习好,脑子好使,她经常对人说,“将来一定要让小妞上大学”。这句话至今在我耳边回响起,心理还是有种暖融融的幸福感。
在我们这个家里,四个姐姐,就有一个是哥哥,母亲固然也会偏疼哥哥了,所以比我大六岁的哥哥自然地会与我发生冲突,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刺,甚至有时也会打起来,可每次以失败告终的总是我,毕竟我打不过哥哥呀!最后还是母亲为我出气,会故作狠状地打哥哥几下,并且批评着他“谁让你学习不如你妹妹好呢?”我知道,母亲已把我的学习成绩视作她的一种骄傲。记得每次我把奖状递到她手里的时候,母亲总会笑得很开心,很满足,但她从没有夸过我只言片语,我知道她是担心我会骄傲。
母亲这种无言的赞赏,更激励了我内心深处那份自尊,那份好强,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否则我拿什么来面对母亲对我的这份袒爱?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落叶飘飞的深秋,在地里干活的母亲突然晕倒,被村人急急送到医院,经检查“胃癌晚期”。当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作“癌”,不明白“癌”会带给人多大的痛苦与绝望。只看到哥哥姐姐经常捂着脸在一边偷偷地哭泣,父亲也不再言语,在一旁一声接一声地叹气。我模糊的意识里也隐约觉察到风雨愈来的恐惧。自母亲病倒,家里再也找不到往日的嬉笑打闹了,气氛沉闷得随时会让人窒息。母亲被病魔折磨得日渐消瘦,脸色苍白,深陷的眼睛没有一点生气,隐约透出一丝对病魔的无奈与绝望。看着姐姐们细心地照料着母亲,而我只能远远地呆望着她,不敢向前,一种即将离别的恐惧胀满胸口,心像被哪根神经提悬了起来,让我喘不过气。
凛冽的北风夹着冰冷的雪花把那个灰色的秋天赶走,剩下了冬的苦涩。一天下午我与以往一样放学回到家,迷茫中看到母亲躺在灵床上,我惊呆了,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在噩梦里,我使劲地扭着自己的胳膊,竟然忘记了疼痛,忘记了悲哀,忘记了与我离别的是我一生最爱的母亲啊!一切像是在梦中,我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我迷失了,孤独的灵魂无依无靠,找不到哪条路才能通往温暖,哪条路才能走到天堂……那个冬天我十岁!
如今经过了这么多年,经过了这么多事,一切又像是在眼前!

 Post By:2011/5/31 11:09:04
Post By:2011/5/31 11:09:04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1/5/31 14:11:15
Post By:2011/5/31 14: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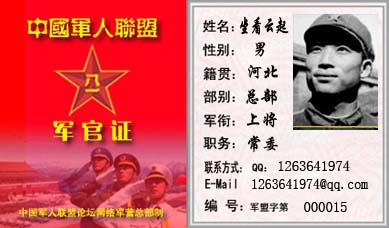


 Post By:2011/5/31 19:32:07
Post By:2011/5/31 19:32:07




 Post By:2011/6/1 5:22:55
Post By:2011/6/1 5:22:55




 Post By:2011/6/1 10:32:39
Post By:2011/6/1 10:32:39




 Post By:2011/6/1 11:49:05
Post By:2011/6/1 11:49:05




 Post By:2011/6/3 6:13:36
Post By:2011/6/3 6:13:36




 Post By:2011/6/3 18:42:01
Post By:2011/6/3 18:42:01




 Post By:2011/6/4 12:23:45
Post By:2011/6/4 12:23:45




 Post By:2011/6/8 14:35:16
Post By:2011/6/8 14:3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