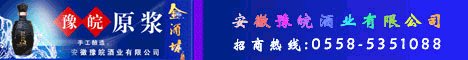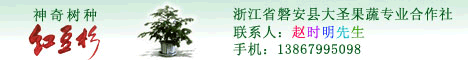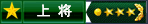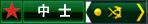十年拚搏奉献,只为续写一段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的动人传说
任何辉煌伟大的创造,无一例外地凝聚着奉献者的心血和汗水。当初,部队刚进三峡,缺水缺电缺住房,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官兵们搭好临时帐篷,草草填饱肚子,来不及睡个觉休息,就上了工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如果按一天8小时工作制和节假日正常休息算,10年时间官兵们整整上了近20年的班。夏天,工地像火炉,机械设备的驾驶室里温度高达50摄氏度,部队配发的竹垫子,不出两个月就被汗水沤烂了。许多官兵的档部湿疹溃烂,但只要还能叉着腿走路,就没有人会躺倒休息。检查内务时,几乎每个战士的枕头底下都有一支皮炎平药膏。在岩石上钻孔时,噪音高达140多分贝,致使许多官兵严重耳鸣。高浓度的施工粉尘,即便是戴着防尘器作业,一个班下来,嘴里吐出的痰也全是泥浆。
往边坡上穿锚索时,几十名官兵“百脚虫”一般扛着60米长、一吨多重的锚索,一点点地向岩石里推进。官兵们的肩膀和手掌上往往是旧的伤口未好,新的划痕又起,一根根锚索就这样沾着官兵的鲜血和汗水被穿进山岩,与船闸融成一体。 焊接闸门时,钢板温度高达60多摄氏度,宫兵们半蹲在十几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内一焊就是七八个小时,飞溅的火花将他们的手脚、胸部烧伤,但没有一人退却。
一滴水汇人江河,就能流淌出波澜壮阔的万千气象;一个人融人整体目标,就能成就令自己吃惊的神奇伟业。
10年间,先后有6对父子、21对夫妻并肩战斗,215名官兵推迟婚嫁,986人次放弃休假,有117名官兵失去亲人后仍坚守工地。每到转业退伍的时候,各级领导就犯难,因为谁都不想走,谁都不愿离开三峡。许多官兵在三峡工作期间,不仅没游览过三峡,连20公里外的宜昌市都没去过。许多人是第二天就要退伍返乡了,头天还在工地劳动。当他们佩带大红花,在欢送的锣鼓声中告别工地时,往往身上还留着未干的泥浆和汗渍。
战士朱树璋,身患白血病,做完骨髓移植手术后,做梦都想着三峡。战友们到医院去看望他,他抱着指导员的肩头痛哭:“指导员,我要活下去,我还要为三峡工程出力,我要看到船闸通航的那一天。”一次,爆破作业刚刚结束,工地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一股奇特的旋风,将副中队长胡浪林连同两吨多重的值班工棚,掀下了15米深的边坡。战士们哭着喊着扒开松土与棚布,只见胡浪林浑身血污,身负重伤。
1995年1月8日,推土机操作手许国宝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工地保养设备,仔细地做着上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他躺在推土机下面给机器打黄油时,推土机前方的土堆突然松动,推土机无声地向前滑动。许国宝来不及起身,战友们来不及上前去拽他。在大家滴血的惊呼声中,推土机沉重的履带从许国宝的身上碾了过去。
年仅29岁的装载机操作手王应保,在父亲去世、小孩夭折、家里的房子被洪水冲毁等多重灾难打击下,很短时间内就白了一半头发。组织上安排他回家,但没出一个月他又回到了工地。中队干部问他怎么不在家里多呆一段时间,他含着泪说:“我的名字里有个‘保’字,可我既保不了家,也保不了妻儿,只能保一份当兵干三峡的责任了。”
武警部队首长视察三峡工地时,对三峡指挥部领导班子给予了充分肯定,许多同志当场流出了热泪。指挥部主任周光奉、助理工程师岑雪珍夫妇俩,更是激动得一夜未眠。他俩说:“我们是学水电专业的,组织上给了我们到三峡建功立业的机会,本身就是一大幸运。现在,总部首长还这样褒奖我们,令我们一生无憾。”
长江三峡再一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永久船闸胜利通航既是世界航运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伟大壮举,为世界工程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三峡永久船闸是世界水电建设史上的奇迹,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是武警水电部队官兵历时10年筑造的一座丰碑。

 Post By:2012/4/1 10:42:17
Post By:2012/4/1 10:42:17




 Post By:2012/4/1 10:43:50
Post By:2012/4/1 10:43:50




 Post By:2012/4/1 10:44:25
Post By:2012/4/1 10:44:25




 Post By:2012/4/1 10:45:21
Post By:2012/4/1 10:45:21




 Post By:2012/4/1 10:45:43
Post By:2012/4/1 10:45:43




 Post By:2012/4/1 13:15:28
Post By:2012/4/1 13:15:28




 Post By:2012/4/1 20:36:40
Post By:2012/4/1 20:36:40




 Post By:2016/5/28 4:08:27
Post By:2016/5/28 4: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