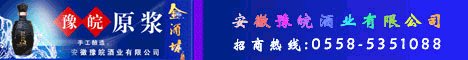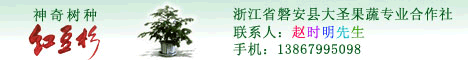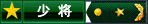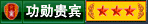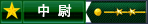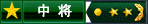第一章 上校军官
你有姓,我有名,
东西南北到军营,
自从交上枪和炮,
共同的名字都叫兵,都叫兵(咳)都叫兵!
俺说的兵,是陆军,陆军也称野战军。最早的时候是红军;以后才叫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战争的时候,咱们解放军就先后组建了西北、华东、华北、中原和东北野战军;1949年的初春,改称为一野、二野、三野、四野;那是多么辉煌的番号。
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到母亲的怀抱。又过了好多年,祖母教我唱民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参军要参解放军”——我就这样朝思暮想地走入了野战军,有了当兵的历史,有了这篇拙作的诞生。
一辆“吉普车”,哒哒哒哒地奔驰在蜿蜒的山道上;
又一辆吉普车,笛笛笛笛地在后面把喇叭按响。
吉普车响,尘土飞扬;
山道上闪过了一棵棵白杨;
前面那辆车坐着士兵;
后面那辆车坐着首长……
蒲公英轻轻地点头,红太阳跃出了山梁,泉水淙淙从山涧流过,大公鸡站在高坡上歌唱。
首长头脑里总是想着打仗,坐在小车里也两眼目视前方。透过挡风玻璃,他把前面那辆车细细端量:啊!新崭崭好漂亮。首长忽然皱了眉头,超过去——看那里坐着啥子人罗!小车司机踩了油门儿——“吱呀”一声挡在路旁。首长一看,面带微笑骂了娘:“郎个搞起的,什么玩意儿车哟!分明是一辆马拉“吉普车”么!首长高了兴,跳下车来细打量,海绵垫,软和和,两排座,稳当当,枣红马肥又壮,车轮滚滚马蹄扬。车辕上坐着一位精干潇洒的小战士,车厢里坐着一个手提包袱,头扎纱巾,身穿红袄,朴实秀丽的大姑娘。
那小战士腼腆地向首长敬了一个礼,然后将马鞭儿一甩,啪啪啪响,一串串柳叶儿掉下来,飞呀飞,飞过山梁飞向营房……
一鞭子甩过了二十年,赶马车的小战士长大了……
回归胶济线
二十年后,我在仲宫理训班学习。和某野战师一团团长薛朝应上校见面时,差点儿没认出来,我们同时“噢”一声之后紧紧握手。因为岁月的磨砺使我们都不是英俊少年了,皱纹已经悄悄地爬上了额头。那时他是团参谋长。我们几乎同时忆起那辆马拉“吉普车”。我是那辆车的创始人和宣传人之一,那辆车奔驰于胶济车站和营房之间,接送千里迢迢来队的士兵的亲人,士兵们就亲昵地给那辆车编了个谣儿:“步兵三团一大怪,马拉吉普跑得快”,一时名传遐迩。
我是在他的新婚之夜离开团队的。他的美丽漂亮的爱妻陈守玉,是我用马拉“吉普”接到营房的。我同乡战友的妻子大都是农村媳妇,唯有他金屋藏娇,娶了个大城市姑娘。当时还没做新娘的她,看见这辆马拉“吉普”,左瞧瞧右看看,车厢里挂着红绸子拴的彩球儿;用红纸贴的双“喜”儿,马头上还戴了一朵大红花儿。她用手摸了摸枣红马,又拿马鞭儿向空中甩了个脆响儿,欢乐的笑声响遍车站。最后她操起鞭子,亲自驾辕,弄得我成了大红脸儿。她却嘻嘻笑着说:“兄弟,我可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呀!驾——”
说起来有缘。在仲宫我又见到了“军事训练先进团”的二团政委朱志仁上校。他是南京市人,工人家庭出身,兄妹八个,住在鸡鸣寺那里。文化革命时,父母怕孩子出去胡闹,每人买了一件乐器练着,他学小提琴,从此和文艺结下不解之缘。据我所知,他干了很长时间军里的文化干事。上任伊始,组织声势浩大的野战军歌咏大比赛,全军业余演出队十八般乐器齐上阵。战士们亮开歌喉,歌声和铜管乐一齐交响,汇成恢宏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飞向蓝天太空,那辉煌的场面至今想起来仍然荡气回肠……
朱志仁用他那宽厚有力的大手握着我的手,略带点沙哑的嗓音说:“哎哟,施实同志,久仰,久仰,你的名字和马拉‘吉普’一样响亮。”“响亮个球呢。”我在心里说。我从步兵三团调走时,没有穿上四个兜干部服。一晃二十年了,我那儿也没去,躲进了小楼成一统,爬我的格子,写我的稿子。说起来也是马拉“吉普”把我拉上了文学的宝座。我把马拉“吉普”的故事编成文艺节目到处表演,谁又能想到马拉“吉普”会演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呢?
我和他们见面,可以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兵营里除了同乡亲就是战友亲,关键时刻比兄弟还要亲。我们那一茬兵,在军营里所剩无几了。农村兵大部分在家“刨地球”了;城市兵当然各显其能了,混得好的也有;在部队的大都上了师团岗位了。仲宫这个地方冬暖夏凉,绿树成荫,上完课休息时学员们纷纷散步,在院外经过一片果园菜地,就是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光滑圆润的鹅卵石像一个个鸟蛋。我们常常在夕阳余辉中,用鹅卵石击水;月光下坐在小河边聊天,二位上校团首长给我讲当代部队官兵的新鲜事儿,我的心就有点躁动。
上过战场的人总忘不了打仗,聊天当然离不开这个主题了。八十年代全球有十大战争,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南疆之战。尽管双方边贸如今已经开通,地雷也已扫除,但我的老部队曾经“潇洒走了一回”的壮举将载入史册。当时有人这样形容我部在南疆防御作战中的情况。一团在地狱,二团在天堂,三团在人间。所谓天堂者是指L山主峰,居高临下,阳光明媚,敌人望而生畏;所谓地狱是L山脚下的N口方向,那里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是最低洼,最艰苦,苦不堪言,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地雷密布,火力交错,阎王爷的生死簿随时能点到你的名字;三团坚守L山半山腰S岭方向,上有天堂,下有地狱,仅一步之遥,虽说是人间,也食不上人间烟火,“两个老鼠一麻袋,三个蚊子一盘菜”倒是不假。
凯旋归来,一团三团都荣立了集体一等二等功,二团啥也没立着。不过他们从山头抬下来一块石头,石头上镌刻着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L山主峰”,他们卧薪尝胆秣马励兵,两年后被树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团”,那块石头如今放在团史荣誉室放出熠熠光华。
战争是个戏台,任何作家艺术家都可以根据天堂人间地狱的故事去想象,去编撰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我的老部队在所有轮战部队中仗打得最多,坚守时间最长,“531”一战,对方发起大规模进攻,虽然首战告捷,但丢失了两个哨位。这不足为怪,不是什么斯芬克斯之谜。
因此,我想入非非,神思恍惚,理论未学进去,成天想构思个作品什么的,冥思苦想,忐忐不安。两位上校说,难道你当了作家进了城,忘了咱们基层官兵不成。于是有一群美丽鸽子在蓝天上飞翔的那天,我坐上由济南开往青岛的齐鲁号列车,飞驰在胶济线上。凭窗眺望,远山近岭,峰峦叠嶂,思绪翩翩。
这些山头我几乎都爬过。我在步兵团待了八年,又在步校当过学员,野战训练几乎都在山里进行,我的老师长就是在山头上去世的。
那天老师长亲自组织山地作战实兵演习。北风呼啸,寒风刺骨,他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士兵们站在群山下,他屹立在山坡上,给全师指战员作动员,嘹亮的声音在大山中回荡: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吗?顺着我左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沂蒙山脉,顺我右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莱芜山脉和泰山山脉。解放战争的序幕就是在这些山脉拉开的。1947年10月,我华东野战军在临沂以北,胶济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广阔地域内,纵横驰骋,密切协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莱芜战役。国民党军集中华东地区的全部机动兵力,分西、北两路,进犯华东野战军总部,华野首长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指挥主力部队隐蔽北上,突然出现在莱芜、吐丝口之间,一举包围李仙州集团,激战三昼夜,歼灭敌46军,活捉军长李仙州。四五月间,敌以三个兵团的主力并肩向新泰、蒙阴一线进攻,企图在沂蒙山区围歼我军主力部队。在毛主席和军委首长的指挥下,我华野各纵队活跃在沂蒙山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实行“耍龙灯”式高度机动回旋,积极寻求制造战机。那时候我们除了参加过一些零星战斗以外,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爬山头”,差不多天天都要走七八十里山路,有时一天走一百多里。干部战士们轻装疾进,歌声嘹亮:“野战军,好威风,浩浩荡荡大运动。爬高山,越高岭,南征北战在华东,英勇善战人民的兵”。
在孟良崮战役中,我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命令各纵把所有的预备队统统拿上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攻上孟良崮主峰。指战员们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沿着陡坡、山脊杀开一条条血路,把红旗插上孟良崮主峰。全歼敌一律美式装备,曾为国民党南京总统府的卫戌部队,号称“御林军”的整编74师,击毙师长张灵甫。就在这时,连日干旱炎热的孟良崮山区,突然乌云翻腾,暴雨裹挟着冰雹恣意倾泻而下,崮上崮下的浓浓硝烟转眼之间被荡涤一空……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吗?
“野战军——”千军万马一齐呼喊,似风雷激荡。
那天师长讲完话,山地作战演习开始了。我们很快进入冲击出发阵地,然后嗷嗷叫冲上山头。忽然天降大雪,鸟雀停飞,杀声戛然而止,这时只听连长大喊:师长去世了。师长去世了。
师长心脏病突然复发,他倒在山头上。师长没有牺牲在战场,却倒在训练场。顿时满山遍野一片雪白,士兵们将松柏野花扎成一个个花圈,紧紧围绕山头,然后脱帽致哀,向师长告别,刹那间,一个个花圈好像碧雪梅花傲然怒放……
后来得知师长名字叫刘振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23 18:07:14编辑过]

 Post By:2011/1/22 21:59:01
Post By:2011/1/22 21:59:01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1/1/22 22:11:53
Post By:2011/1/22 22:11:53




 Post By:2011/1/22 22:15:01
Post By:2011/1/22 22:15:01





 Post By:2011/1/22 22:32:22
Post By:2011/1/22 22:32:22





 Post By:2011/1/22 22:36:51
Post By:2011/1/22 22:36:51




 Post By:2011/1/22 22:38:07
Post By:2011/1/22 22:38:07




 Post By:2011/1/23 1:12:13
Post By:2011/1/23 1:12:13


 Post By:2011/1/23 10:05:48
Post By:2011/1/23 10:05:48




 Post By:2011/1/23 12:00:11
Post By:2011/1/23 12:00:11


 Post By:2011/1/23 12:00:43
Post By:2011/1/23 1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