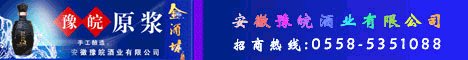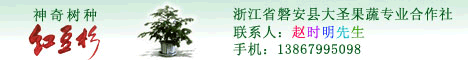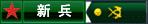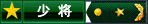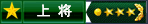生命的白雪
生命的白雪 ——风之叹息 棉絮般的雪花落入我的眼中,晶莹地融化了。 我感到细微的痛,麻木的。 有个声音曾对我说过,你的瞳仁是银白的颜色,就如那雪。 这个著名的医生断定我还有几小时的生命。他不是冲着我说的,但我确确实实听到了,他对雪儿说的。 医生进来了,麻利地收拾好医具,向我打声招呼就要走。我躺在乏力的床上,轻轻地唤住了他。“医生,”我用浑浊模糊的眼睛注视了他良久。“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还有多长时间?”医生摆出一副自以为很轻松的样子说,“您放心,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我苦笑了一下,他到底没有说真话。有谁会对一个60岁的老太太讲真话呢?我吃力地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走了。不一会,就听见重重的关门声。我扭过头,望着硕大的窗帘不加掩饰地覆盖了视野。模糊的。一切的一切,都好像在演戏一样。 昏昏沉沉好一阵后,雪儿突然叫我。她扎好了围巾,一脸兴奋地告诉我,外面下雪了!然后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望着我。我笑了笑,“你可以去看看雪。”她欢呼雀跃地去了,于是我就又听到一次重重的关门声。 我费力地从床上爬起来,拉开厚厚的窗帘,看在最后几个小时的最后一场雪。看在呼啸的北风中凌厉不已的狂卷的雪花。它们在四处游荡着,一群一群地堆聚着,在房上,地上留下征服后的轨迹。弯弯曲曲,寒颤不已。 在厚厚的雪层密集的地方,我看见了雪儿,那个让人怜惜的孩子。她戴着手套,在认真地堆雪人。 一片雪花沿着窗滑过轨迹溜过了,溜过了我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溜过了60年光阴的足迹…… 我五岁了。已经能呀呀哼哼地唱很多好听的歌了。我知道,自己比四岁年长了,但却仍然改不掉顽童的个性。那时,我喜欢冬天,喜欢冬天里凉飕飕的感觉,贴着脖子滑过,亮晶晶的玻璃似的,还有,就是冬天的雪,被雪覆盖后大地的景色。冬天,老师让写雪的作文,于是我就写雪纷杂地躺在地上,冰糖似的,亮晶晶把大地装扮的很好看。老师看完后说这句话不行,雪落在地上怎么会像冰糖似的,还有这句话写的罗嗦,只要直接写雪过后,大地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就行了。老师说的我不爱听,于是我就反驳,雪的确是亮晶晶的,而且您怎么知道雪是银色不是白色的呢?如果雪是脏的,那么大地就不是银装素裹的世界了。老师的脸被气得铁青,她指着我的额头,你呀你,怎么这么没有想象力呢?像冰糖好听怎的?我不听,仍旧写我的冰糖。一直。 我的手在颤抖,雪儿就好像年轻时的我。我悲哀地想,如果不是因为多病自己会出去的,因为我是这么地爱着雪,爱着被雪覆盖的大地。 我的童年没了。因为我上了中学。整天忙忙碌碌地穿梭在学校和家的中间。每天都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做。我告诉自己,忘记一切吧,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但,我仍然忘不掉曾给我冰糖般的乐趣的雪和被雪覆盖的大地的景色。我一直在盼望着,盼望着雪的到来。 终于下了第一场雪。当那洁白晶莹而又四处纷飞的雪花肆虐地落到被征服的屋檐,枯树,大地上时,我感到快乐。我感到雪在融化,然后进入我的身体,直到我的瞳仁是银白色的。可惜,这次我没能尽情地在雪中跳舞,因为老师又在发卷子了。我叹了口气,再次警告自己,不准想别的,好好学习。可当我拿到发下的卷子时,那白的透明的颜色又让我窒息,我想到雪的颜色也是这个样子的。原来,那不规则的雪花形状是一张张不同的卷子啊!我向窗外望去,远处的房已在漫天尖啸的雪中变的迷雾般模糊了,一层一层涂抹上去,像一幅幅透明的油彩画又像是山涧间空灵地颜色。虚幻的。我打开窗子,让在狂风中肆虐飞舞的雪花打在脸上,落在瞳仁里。我伸开手掌,试图抓住一片雪花,看看它的形状,但雪落在手里,软软地化了。 我拼命地在想一些事情,也许,过不久,连想的资格都没有了。我掰着皮包骨的僵硬手指,触摸着窗外雪的味道。 我上了大学。之后参加了工作,但似乎什么都不太顺心,扭着的。工作上我的老板对我很苛刻,几乎到了痴狂的程度。我开始讨厌以前喜欢的一切,惟独雪和雪后大地的景色。今年的冬天来的很迟,但雪却下的很早,也很大。我曾独自坐在一家穷酸的小店里。呆呆地望着雪徐徐地落。天阴阴的,不带杂色。雪就星星点点地从那里落下来,再落下来。然后触到地面,闪电般地消逝。我很奇怪,雪怎么融化留不住了?这难道亦如我愉悦观雪的心情?远处的屋仍是屋,也没有烟雾般的笼罩了。 我微微侧弯下身,拾起地上的一支笔,在手上费力的写下几个字。这时,门重重地关上了,雪儿回来了。她进了屋,看着我突然就尖叫起来,“婆婆,您眼睛的瞳仁是银白色的!” 一小时后,医生说这个穷酸的老太婆已经死了,她有个捡来的孩子叫雪儿。 这个老太婆手里有字——60年的雪。
----后记

 Post By:2017/11/27 10:21:13
Post By:2017/11/27 10:21:13


 Post By:2017/11/27 13:05:05
Post By:2017/11/27 13:05:05




 Post By:2017/11/27 13:17:03
Post By:2017/11/27 13:17:03




 Post By:2017/11/27 17:32:18
Post By:2017/11/27 17:32:18




 Post By:2017/11/27 20:28:35
Post By:2017/11/27 20:28:35




 Post By:2017/11/27 20:46:26
Post By:2017/11/27 20:46:26


 Post By:2017/11/28 5:37:15
Post By:2017/11/28 5:37:15




 Post By:2017/11/28 10:43:46
Post By:2017/11/28 10:43:46




 Post By:2017/11/28 11:44:54
Post By:2017/11/28 11:4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