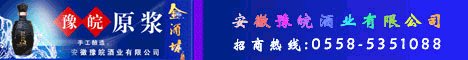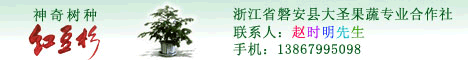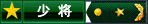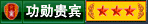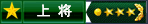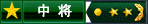第五章 望断南飞雁
一条清澈的小溪, 从高山上流下, 来吧,洗去征尘, 在这男子汉的世界, 挺起那勇士的胸膛, 露出那男性的肌线, 扭曲着赤裸的身体叫着: 我是罗丹的“思考者”……
大炮上刺刀
凡到过前线的人,都会听到过一个距国境线很近的我方一侧小村的名字。没有一个炮兵不是自豪地提起这个名字。没有—个步兵不是敬重地提到这个名字,现在这个小村当然已经繁荣荣起来,边贸的热闹淹没了战场的痕迹,但那时一米多高的茅草覆盖着阵地,还不时有画眉鸟光临。阵地前数百米深的陡峭石壁下,是曲折婉蜒的B江。隔江向南俯视,一千米外的L山前线的最前沿阵地,L山战场最激烈的热点尽收眼底。 这是一个凌晨,末班哨正准备叫醒战友抢修火炮工事,对方对我前沿阵地又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恰好开始了。 天刚蒙蒙亮,对方大约一个连的兵力,分别向我两个阵地进攻。我轻便炮群立即以炮火压制;二营的炮连压制进攻左翼阵地之敌;一、三营炮连压制进攻右翼之敌;团的炮兵切断后路把敌后续部队阻隔在原地;师炮团火箭炮压制敌人的直瞄火炮。这是一次精彩的炮战,大小炮**弹准确地落在敌群。步兵在阵地上看着大片的敌人倒下了,跳起来呼喊:“打得好!”炮兵万岁!” 数小时之后,对方又以两个连的兵力,从三面重点进攻我另一个阵地,并以一个排的兵力佯攻他们第一次进攻的左翼阵地。我方采取切头、断尾、中间聚歼的手段,将对方的大部分兵力阻隔在我阵地前一百米处,然后实施各种炮火的火力急袭。数干发炮**弹落在一个地方,那里一片烟尘,一片火海,什么也存在不了!对方的第三次进攻也被我打退。 天色黄昏。对方又以一个连的兵力,向第一次进攻未得手的左右两个阵地再次进攻。我轻便炮群的炮口喷着复仇的火焰,将炮**弹准确地送到敌群,将敌人全部歼灭于我阵地下的一个山腰。这里顿时变作对方的一座巨大的坟墓。 黎明,“李海欣高地”方向,对方又开始向我阵地冲锋,战斗立即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那个最前出的哨位里,只剩下后来被最高统帅机构命名为“战斗英雄”的战士韦昌进一个人在坚持战斗,哨位的石洞被对方的炮火炸塌了,仅留下个小小的洞口,韦昌进身负重伤。这时二营营长曹汉在报话机里告诉他:“韦昌进!你不要害怕,我让炮兵支援你,一定给我守住阵地!”这时,韦昌进用他那仅存的一只眼睛,清楚地看到自天而降的火力屏障。在哨位的四五米外,是小口径火炮围起的第一道火网,在二十几米外,是各种口径直瞄火炮打出的第二道火网,在高地周围,是大口径曲射火炮布下的第三道火网。冲锋的对方士兵完全被火网包围了;最后留在战场上的是数百具尸体,和留在一名中国士兵手中的光荣阵地。 上述是薛朝应向我描绘的“7.19”大战情景。他说: 9.8战斗我在小村配合张建华奇袭“211”,指挥炮兵协同。 小村有东高地,西高地。我在炮阵地上指挥炮团重炮连,师炮团两门高炮,我团高机连两挺14.5高机,还有12.7高机两挺、双三七高炮两门。所有高炮、高机瞄准,定好诸元,对准打。 战斗开始时,浓雾弥漫,上午十时左右的大雾把整个高地遮盖在纱幕之下。但炮手们早把目标诸元记得分毫不差,简直是半个密位都不会误差的。突击分队的指挥官提出要求是,从步兵呼唤炮火到炮兵实施射击,必须在十秒内,差一秒也不行,而且要指哪打哪儿……突击队长对炮兵连长说:“老兄,我这次生死就在你们了!”炮兵连长只回答一句话:“好吧,你们要炮火支援,就说吃‘土豆’行了!”果然,步兵刚一呼唤炮火,炮兵们就把炮**弹准确地送了过来。步兵指哪儿,炮兵就打哪儿!二十五个火力点在眨眼之间,已经被他们摧毁了二十二个。前头的副连长原明离山顶只剩八米,突然,在他头顶上有一挺机枪叫起来。‘XX目标——土豆!”后来被最高军事统帅部命名为“战斗英雄”的原明说,那情景简直是神了,在短短的十秒内,两发炮**弹就送过来了。而且打的是离原明只有六、七米的火力点,第一炮把火力点打哑。第二发纯粹是为了保险起见。冲击的突击队员们通过报话机,一个劲地喊:“暂停,土豆充足。” 被炮兵打傻了的敌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击队员们已经冲上来了。 在一号哨位的左上方不到五米的地方,有一个我方观察不到的对方哨位。那里天天向一号哨位扔手榴**淡,一号哨位天天人员负伤,可谁也看不见敌人在哪里,投手榴**淡的敌人非常狡猾。我在西高地上慢慢观察,终于一天看到1号洞顶上有五个人在修工事,那洞在一个反斜面上,很隐蔽。我让八五加农炮连连长李宁观察,他们也观察到了。连长李宁守在四十倍望远镜后面,耐心等待,终于又发现那手榴**淡是从一块大石头后面投下来的,修的工事是假洞,没有人,判断大石头后面有越军哨位,决定敲掉它。师长在电话里问:这么近的距离上射击,我们哨位里步兵的安全有保证吗? 李宁回答:“绝对的保证没有,但有信心。”师长说:“好吧,我同意你们打I”步兵们说:“你们放心打,我们不怕。”一号哨位正冲向小村炮兵阵地,五米,火炮技术散布,气象条件的影响,偏流,炮膛磨损,火炮空回……射击教员能一口气讲十几种影响命中率的误差,可在这里,这一切误差加起来不但不能超过五米,而且考虑到炮**弹的杀伤威力,连两米都不能超过。从南京炮校来的排长熊昌建亲自操炮瞄准。为了绝对地保证步兵安全,火炮瞄准八米见方的大石头左侧,一点点从左向右打,从这个位置打,炮**弹也许会从石头上面飞过去,但绝对打不着我们自己的哨位。第一发炮**弹削去了石头的一个角,第二发炮**弹又削去了一块。观察镜看到了露出石头的一块木端。步兵在报话机里喊:“对,就是这个位置。”又是十五发炮**弹飞过去,一点点像剃刀一般,把一块八米见方的大石头全部削去了。敌人哨位的洞口显露出来,第十八发炮**弹毫不客气地飞进去,不是一发炮**弹的爆炸,而是把里面的弹药全引炸了,一根根木头被掀到山下,敌人的尸体飞到四五米高…… 后来,八五加农炮连被最高军事统帅部命名为“英雄神炮连”。 薛朝应建议我去采访炮兵。他说在未来战场上,大炮的威力会越来越大。即使海湾战争高科技大汇演,电子科学应用于现代战争中,但伊拉克和美军都没有忽视导弹和火炮的杀伤威力。仅伊拉克就部署3000门火炮。我们打的那场局部战争,在那样复杂的地形上防御,光靠前沿很少的步兵,没有火炮的威力是难以想象的。 我见到了高炮团长姜兴民。高大的身材像大炮一样威武。别看他手下掌管着一门门大炮,可是说话却慢声细语,不是炮筒子睥气。他说:“6.11”失利,军命令高炮打平射,拉到L山东北方向,压在国境线上设了一门潜出高炮,压制对方火力点,那门炮威胁很厉害。把对方机枪炸飞到天上。潜出高炮一发射,后边曳光,敌人说这是导弹。炮阵地设在山坡反斜面上,被复三米,有人员隐蔽部,敌人根本打不着。为了摸清敌人炮阵地,我们用航模飞机改装之后,装上照像机,潜出照像40多次,照成9次,照了二百多幅侦察照片,对敌人威胁很大,把防御工事、堑壕都照下来了,那时我当炮兵营长,第一次飞行侦察,对方没有反应,第二次提出抗议,说我军用高空侦察机,实际上是搞的航空模型,对炮兵瞄准很管用。 我到地炮团已是下午,团长政委都不在,政治处主任让宣传干事孙一军陪我去看神炮连。一路上他向我讲了好多传奇。 比如说,抓到越军俘虏时他在那里,那个家伙只有17岁,是个副班长。九点多钟审问他,给他喝啤酒,他不喝。开始不说话,后来吃饱了喝足了提出要求,不要告诉那边人他被俘 了。他家有姐姐妹妹,他是独子。那边规定,每家必有一个当兵的。是女的也要去。所以越军有不少女炮兵连。说他在炮阵地上经常看到越南女兵在河里洗澡。沿着B江南岸流向清 水河畔的拐弯地方,可以看到奇观。晨阳微露,雾起江面,如轻纱漂渺升腾,经常出现一些奇妙的女人的裸体曲线,像中国古代舞蹈中的造型,像是罗丹刀下的人体雕像。炮兵们不止一次发现,但都保持着沉默,谁也不愿意破坏这近乎自然的美。如果谁看见了就哼两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两相情意深,共饮一江水。”开始还打两炮吓唬吓唬,后来不打了,随她去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刚吃了饭,在掩体内,突然“咣、咣”两发炮**弹在洞内炸响,炸伤炸死我们不少人,副营长肠子都流出来了,营长被一块弹片削进头部当场牺牲。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敌人用的美人计。目前不少国家都有女兵,海湾战争大批女性开赴海湾地区;据说50多万大军,女性竟占1%。许多国家对此有争议,论说纷纭。 吉普车驶进炮营。我看到了大炮昂起头颅,披着绿色战衣。孙一军给我介绍哪些火炮上过战场,哪门炮立过战功,哪门炮在战场打红了炮管。然后他带我去看导弹连,可惜军械员不在,看不到导弹了,他却向我讲起了打掉人家导弹的传奇人物。 那个人就是有点传奇。他以他爱思考的脑袋带出了一个全能炮排。那次最后考核,他们连进行射击表演,如果把炮**弹都打到半径为十米的白色圆圈内,他们连就可以当之无愧地上前沿。射击开始,不管是他的三炮还是他的四炮,都是第一发炮**弹就准确的送到白色圆圈的中心的只有脸盆大小的白点内。继续射击,800米到3000米的六个目标,全部是一炮摧毁。师长说了一句:“有这样的炮兵上去,我就放心了。”返回的路上,他一时高兴,把司机赶到了一边,亲自驾驶起来东风牵引车。小雨把道路弄得贼滑,他的车毫不减速。突然前方迎面开来一辆摩托车,也是飞快,他急忙一刹车,可是贼滑的路,使他的车猛掉了一个头……没说的,军纪如铁,他落了个记过处分一次…… 在阵地上,吃水是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炮手们为水曾经付出血的代价。他就琢磨怎么从几百米外的山坡上,用塑料管把一眼山泉里的水引到炮位上,不仅解决吃水问题,还用一个 底部钉眼的空罐头盒接到塑料管的这头,吊起来是一个很带劲的淋浴喷头。他还在火炮工事射击孔上装了可以吊上吊下的活动防弹钢板,设计了工事内的小工事…… 敌人为了对付炮火的致命威胁,在正面的阵地上,设置了五具“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发射架。开始炮手们还没有留神这种小玩艺的厉害,有一天一枚导弹竟然“突突突”地从射孔钻进来,然后又从工事门口钻出去,在工事外炸响了。 他透过瞄准镜观察,发现了对面阵地上六个敌人躲在一块大石头底下,发射架上又架起一枚萨格尔导弹。当时他的心情确实有点紧张,这种导弹显然比敌人的直瞄火炮更准确,它以射击坦克之有效而闻名,如果火炮工事被它击中,显然不会比一辆钢铁坦克保留得更加完整。他非常熟练地操纵火炮瞄向那个发射架。但当他就要发射时,他突然又把瞄准点抬高了一点,他是零点几秒内决定下来的射击大石头。一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大石头,这一发炮**弹恰好把大石头轰塌了,六名敌人连同导弹发射架都被大石头盖在底下。他呢,又轻轻松松地补上一发。 此后,打导弹成了他的专职任务。一发现导弹,就由四炮打,四炮打导弹必然要他瞄准。导弹厉害还是火炮厉害?按理讲还是导弹厉害,可在这里,加农炮绝对地厉害。 他接连打掉三具导弹发射架后,徐德彪也捞着一次机会,而且真被他打掉了。再之后,三炮也捞着一次机会,也打掉了。再再之后,对方的导弹再也不敢露面了。代之而来的是敌人直瞄火炮和曲射火炮对他们的覆盖式报复,有一块弹片不偏不斜正打在四炮炮身管正中,把炮身管穿了一个透明的窟窿,这在炮战历史上恐怕也是稀有之事。连队为他报请了二等功,但 迟迟批不下来,听说主要是参考他以前的那个处分。但没想到最后批下来的却是个一等功。 炮兵老大哥声威赫赫,战果辉煌,因此阵地上落下的炮**弹也空前。每个炮工事都有敌人的炮**弹、导弹钻进来过的事情,奇迹是竟没有一个因作战阵亡!说出来真难令人相信,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这种奇迹,谁也难以相信。 7月的一天,敌我双方的直瞄火炮进行着激烈的对射,一炮用十二发炮**弹敲掉了对方高地上的右二炮。对方集中了两个设置在远后阵地的炮兵连一一130加农炮连和152榴**淡炮还击一炮。一发152炮**弹不偏不斜落在一炮炮身管(身管被炸弯,呈弧形指向蓝天),然后穿透防盾,落在一班长的脚前三十厘米处,裂成两瓣儿。这是一发臭弹! 在另一次炮战中,三炮连续发射了八十余发炮**弹,装弹手王洪平累得实在站不起来了,副指导员焦守云让他到掩蔽部里休息,他坐在大架上喘着气说:“我实在站不起来了,死就死在这里吧。”说时迟那时快,一发炮**弹已经飞进射击孔,焦副指导员只见眼前火光一闪,心说:“不好!”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醒来时,一睁开眼面前一片黑暗,他想:“坏了,眼睛瞎了。”他摆了摆头,看见了射孔处透进来模糊的光亮和充满工事的浓烈硝烟。哎,没瞎!他活动活动腿:“哎,腿还能动!”他冲出工事,就跑到连部报告去了。三班长贺国新感到炮声不对,钻出掩蔽部来到工事里,看到趴在地上的王洪平和贾其章,心里说,“坏事了!”他过去拍了拍王洪平,王洪平动了动,又过去拍了拍贾其章,贾其章也活动了。王洪平和贾其章爬起来就喊副指导员。喊了几声没见回答,他们以为副指导员已光荣牺牲,也跑到连部去报告。看到副指导员在连部,一屁股坐到地上,叫道:“哎哟我的副指导员哎!”事后检查,三个人连皮毛都没伤一点。这发炮**弹装药受潮,只炸开了几块。 还有无数次这样的传奇经历惊险故事…… 炮**弹落得多,自然奇事出得多,他们几乎天天打炮,天天摸炮,步兵打大仗,他们连续打几天炮,三个人一班轮着打。步兵不打,他们也打,打火力点,打屯兵洞,还和对向他们的十门直瞄火炮直瞄对打,胜者还是他们。军区前指张太恒司令员在一篇文章中说过:“L山战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炮战。”他还说过:“在这场特殊的局部战争中,最能代表现代战争的特点是炮兵。” 难怪前线步兵们对炮兵老大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候,呼唤的是向我开炮。当亲眼看到炮兵弟兄们为他们扫除障碍时,又要迫不及待地在报话机里用明语呼叫着:“真打炮了!炮兵全体同志们万岁!” 笔者来到那个神奇的八五加农炮连,见到两位年轻的主官,我提出要看看立下战功的八五加农炮。他们说,早已换装啦!他们已经改编成反坦克导弹连了。但荣誉室里仍然挂着中央军委授予的“英雄神炮连”的锦旗,总参谋长张万年不久前视察了该连,并亲笔题词:“英雄连队,再立新功!”
奇袭,十六分钟
“7.19”一战告捷,大功团打了一个翻身仗,威震南疆。“211”高地曾经是全师指战员的一块心病。大功团丢失哨位的耻辱,该到雪耻的时候了。八年之后,张建华已当了大功团的副团长,我到他宿舍,沏了一杯龙井茶,我们彻夜长谈。他说: 我从师里回来准备一下,带着兵上了255屯兵洞。 奇袭队组成后,由师侦察连副连长原明和副指导员贺先明分别担任正副队长。 这里有一段插曲。“7.19”,李洪程参谋长在团里代理团长,他和我通了好几次电话。我的10瓦单边带电台突然听出两个加强营进攻,韦昌进6号哨位丢失。6号哨位是“111”阵地前出哨位。我一听这个哨位丢了,急了。“陈昌建,听到没有。”我对二营副营长说,“把60炮调出来,对‘111’高地6号哨位。你标好山头。”他不同意。我说陈昌建,这可是全局啊。我把所有电报抄下来说:“你看。” 陈昌建说:“咱这里够意思啦,一出来就有伤亡。”我说,保住“111”,这是大局,对于攻打“211”也好协同。他同意了。我指挥把一门炮架在255高地,这时111高地没有动静。我说,等一会儿,叫打就打。这时又接收到6号还在。我让60炮对准6号哨位表面阵地打。敌人也发现了目标。陈昌建刚撤回来,忽然敌人一发炮**弹打来,爆炸,那炮没有了,炸飞了。下午四点,光找回炮盘来。 到了傍黑天,对方又进攻。2号观察所观察到,对方在小前山有指挥官,二连一炮从洞里炸出两个敌人尸体,夜间又打了几炮,把一个弹药库引炸了。 到了夜间,离146最远60米,听到146有对方袭击,说听到电报信号,怪了。对方迂回我应该看到。不可能有行动。我晚上又出去两次,拿40倍观察仪,没有情况。我告诉146放心,没有发现情况。 李参谋长说,建华,你敢担保吗? 我说参谋长,我在2号观察所顶端一侧,如果有敌人踩石头,滚也滚到我脚下,我用夜视40倍看的,绝对没有情况。 7月22日撤下来没有出击。 “7.19”打胜了,各级很高兴。又定到8月底打“211”。结果上去也没打成。军里传真,对方有新的活动,没动。 中间搞了一次偷袭。 8月19号,正式出击偷袭,提前一天屯兵。白天,班长王祥龙带战士孙德栋,徐健第一次摸到二号哨位抵近侦察。他们手脚并用,轻轻地向前爬,在不到三十米的距离上,排除地雷七十多个,检掉几百个钢刺,一直爬到离二号哨位只有四米的地方观察了地形,选择了方位物,安全返回。摸清2号哨位,带回冲**锋**腔、水壶。当时怀疑2号到底有没有敌人?搞了一次偷袭,证明白天没有敌人。天黑之后,对方派人占领,白天不占,夜间占。 抵近侦察之后,侦察兵们又在沙盘上反复推演;又在与211高地地形相似的采石场上,苦练秘密接敌本领。二十七名奇袭队员都磨烂了两套军装,半数以上同志的手、肘、膝等处都破皮烂肉。他们每天都要头顶烈日,在四十度高温下苦练翻山穿林、摸爬滚打。8月27日,奇袭队屯兵“255”1号哨位。 9月8日早晨,天刚亮,7点开始下雨,9点下得很大,雾气浓浓。那几天战场特别安静。我前出1号哨位,奇袭队沉不住气了,怎么还不打? 9点40分,我从1号哨位下来。拿起电话,王兴辉接电话,我说,团长,这段时间天天观察,士气好,时机好,战局好,能不能请求首长出击。他说,你等一等。我请示师里。李副师长接电话。他说,要打了,不能再等了。我说,等,等,什么时候是一站。你打也好不打也好,对不起,副师长,你后边不动,我前边动。把电话挂了。我说,高参谋,10点钟准时出击,报告师长。陈昌建给师长报告,师长正好到军里参加作战会议,到军里去了。我把电话要到军作战办公室,师长一听,等等,我马上回去。 李副师长命令我,建华,电话不能放。 我左肩对“211”,右肩直接和李副师长通话。肩膀用胶布缠着话机,手拿夹子。 师长马不停蹄地回到师里问:老李,怎么啦,要动。 李副师长说:师长,前面非要动,有什么指示? 师长说,你们动了还有什么指示?打了就打。 李副师长对我说,建华,出一个,报一个。 这时候侦察员一个个穿裤头背心,整装待命,箭在弦上。 我说,副师长,来不及,怎么报? 副师长命令:不行,出一个报一个。 我说,老高,老陈,战斗发起后,你们实施指挥。我到一号观察所。我穿上衣服,绑着手榴**淡,带着微冲,微声手枪,十瓦电台,十倍望远镜。我选了两条路线,一是通往“211”右边,紧贴146下面。二是从东侧迂回过去。一切准备充足。 这时全师9个炮兵营,8个作好战斗准备。 炮兵炮**弹握在手里。 炮上膛,绳拉紧,听我口令一齐放! 正常是炮火准备,步兵冲击。这回打破常规,我一炮不发,侦察兵先上。按计划,第二突击队在2号洞离1号洞相距13米。 第二突击队将爆破筒填进去,拉火7秒钟,正好爆炸。 指挥员命令炮火准备…… 李副师长说,建华,我等你说,放,我同时命令炮兵。 我报告,出击了,一个啦! 二个啦! 三个啦…… 师作战室。 师长端起茶杯,在作战室踱步,作战室显得紧张,又显得轻松。师长喝了一口茶问: “到什么位置啦?” 李副师长:第二突击队围起了2号。 我报告:第三突击队到了三号。 第一突击队正准备向一号出击。 正说着,第二突击队一拉爆破筒。 我报告,放! 李副师长命令:放! 就在爆破筒填进去,一拉引火索,即将爆炸的一刹那,8个炮兵营一门门大炮的炮**弹同时出膛,虎啸山鸣,天崩地裂。同时炮响两个小时,顿时山石横飞,山头化为平地,阵地周围被炸成锯粉。 大白天出动,对方不知我们攻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侦察兵16个人前后不到16分钟夺取全部哨位。 这时对方反应过来,将所有炮火集中到“211”“255”高地。硝烟弥漫,陈昌建和我谁也看不见谁。 我光着屁股坐在5个罐头盒上,只觉得山在摇晃。眼前黑烟滚滚。当时卫生队邓军医在洞里,心里为突击勇士们担忧。 打到下午两点多钟,侦察兵、工兵一共36人,组成三个突击队全部占领了“211”。战报立即飞往前指。 步兵七连排长许子义等12人全部屯在了三号哨位。还有两个突击队屯在“147”待命。 两点多钟,三号洞炸塌了,引爆了两箱手榴**淡,伤13人。 下午4点多钟,战火平息。我上午去“255”l号洞,靠着一根树休息,这会再去,树没有影子了。被炮**弹炸得连树枝也找不到了。石头像石灰一样全白了。 战斗第一回合宣告结束。突击分队忽然联系不上了。侦察兵884电台不通了。占领情况我不了解。师里来电报速报战果。我回电: “详情待查,稍等。” ——18号。 忽然无线电通了。侦察分队报告,突击队长原明副队长贺先明和部分侦察兵负伤。 师里又来电报,速报战果。 侦察分队不报,人都抢不过来了,怎么报?中央军委发来贺电!一级一级电报发来,速报战果。从中午不到两小时,九封电报,速报战果。 我的代号为18号 18号,18号—— 小张,小张—— 建华,建华—— 来一封,扔一封—— “6.11”战斗说参谋长谎报军情,报个鸟—— 高参谋和陈昌建说,赶快报吧!万一技侦获取…… 师来第十封电报:张建华,你作为一线指挥员,要迅速准确及时报告情况,是你的职责,速将情况给我报来。李 我报:歼敌48名,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武器和物品一部分。 实际上我不知道情况,我报的战果明显是小了。炮兵打了那么长时间,也有战果啊。 这时架线兵李学武不顾敌人炮火严密封锁,接通了有线电话线,壮烈牺牲。前面报来了情况,歼灭敌一个加强连,和我报的没有差别。我直接和李副师长通电话,详报了战情。 天黑下来了。战场上的一时平静,又将意味着新的大战。 我靠着洞壁,闭着眼,想着下一步怎么打?侦察兵伤员那么多,需要赶快替换。我在琢磨点子,心急如焚。我想起三个月前的“6.11”之战…… 那天,我和黄金生副团长前出“255”。 走到洞口,杜参谋问,老张,有什么事给你办!这个时候,不能考虑多,一摸口袋,发票。通讯员买插座发票,一元多钱,给他说,报了交给小唐,战士没有几元钱津贴费,当兵的家庭都不富裕。俺两个出去了。 一出洞二公尺,一个小战士光屁股,爬在那里牺牲了。晃晃他,眼睛瞪得大大的,给他合上眼,头部没有伤,炮**弹穿心脏上了。命令其他人抬走,安放好,我们又往前走。 碰到一个石洞,一副担架,一个伤员,稍等等。有个包着头的小战士,一问是三连的,章丘明水的。同志,哪个部队?战士愣声愣气的,挺白净,娃娃脸。 不认识吗?他,你认识吗?咱们一个部队,团作训股长,这是黄副团长。警卫员解释说。 “不对,不对,不是我们团的,团领导我都认识,你两个首长我怎么不认识?我在连队当通讯员,送文件,哪里都认识。”一听说话,像个江苏兵,错不了。和黄副团长老乡,说了几句话,洞前面一棵大粗树倒了,炮**弹炸的。黄副团长十分感谢小战士,不停下说话,咱们正好在那个位置上。 当天晚上,跟着电话线找,踏着血迹上去的,一路上全是血。上面是个一米多高的陡坡,爬上去,脸盆大摊血,血红血红的。伤员四五个腿都没有了,往上爬,四个小战士抬着重伤员,那两个班长往外送,让一个看重伤员。 到了255高地,遍地尸体,胳膊、腿、头,武器、手榴**淡、子弹,到洞里以后,三营长在里面,他在洞里站不起来。黄副团长爬进洞去,好多伤员,我进不去,闷人,憋死了,当时乱了,突击班,排,建制混乱,指挥层次多。黄副团长传达指示,分期分批上前打,在洞里重新组织进攻。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来电报,让我和黄副团长下去,回到147。黄副团长说,能不能走,炮声不断。我说,我先下,你跟后面。255洞比较高。洞口是个平台,房子那么大,一个烈士在平台上趴着,空爆弹一炸,炸到了头上,头和臂搭拉下来,脑浆流着,残不忍睹…… 那天下阵地,到阵地烈士停尸房,我嚎啕大哭了。这是我上战场第二次掉眼泪。第一次是我带着侦察兵和七连到二线搞模拟训练,研究作战方案,我忽然控制不住感情,掉泪了。上车以后,心想,这一仗又要牺牲多少干部战士,为了让更多的战士见到父母、让更多的干部见到妻子。见到哥哥姐姐妹妹,见到亲戚朋友,我作为一线指挥员,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再有大的伤亡了。 兵力上不来怎么办?只好用直射炮直接掩护。这时你听那方向,高炮“咚咚咚”,85加农炮“咚一咚”——,“105”火炮“嗵!—— 咣!”一响对方老实半天! 阵地上一指挥,马上炮**弹过去了。火力保护,围着半拉山,只要远处发现情况就打炮。 晚上,七连三个突击队上来了,接替了侦察兵,突击队36人牺牲三人,大部分轻伤,从攻到守在阵地上整整16个小时。 9月10号,七连进行了最艰苦的战斗。 班长王雨军和战士李继光、边宝方坚守一号哨位,敌人分三路再次扑来,王雨军迅速跃出洞口,举枪对敌人瞄准,忽然敌人一颗枪榴**淡射向他的背部,他没有倒下去,扣动扳机,一发发子弹射向敌群。李继光,边宝方也跃出了战壕,扔出了一颗颗手榴**淡。十几分钟后,敌人被打退了。李继光、边宝方要背班长下去。王雨军最后一点力气艰难地笑说:“我不行了。我牺牲后,你们一定守住……阵地!”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 武师建,山西文水县人,刘胡兰的同乡。18岁从地方考军校,开始了军旅生涯。他是一位年轻的排长,战士们开始叫他排长老弟,几经沙场,战士们都信赖地称他老大哥了。晚上,敌人又轮番进攻,只剩他一个坚守这个神秘的小洞了,他知道这个失而复得的哨位至关重要。他用冲**锋**腔、手榴**淡迎击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并不时呼叫炮火对敌覆盖。恼羞成怒的敌人一排排炮**弹带着巨大的轰鸣砸过来.洞口炸塌,石块埋住了武师建大半个身子,增援上来的战友见排长被埋,赶紧俯身去扒,可惜已经晚了。他带着对祖国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在战场上走完了自己短暂而壮烈的一生。 刘占忠,山东定陶人,一名普通的小战士。从“5.31”到“9.8”,三进三出“211”,被称为与阵地同在的钢铁勇士,一人坚守“211”1号哨位4天5夜,火线入党,火线提干,军首长都为他的勇敢精神感动得流泪。他现在是7连副连长,至今体内还藏着十几块弹片。 9月15日我把指挥权交给了三团三营张建国,郭本年。七连班长张西礼接替了一号哨位。 9月15日下午,命令我下阵地。 我站不起来了,两腿像瘫痪了。陈光辉和警卫员拖着我。把手枪和微冲带着,穿上军衣,把枪扎在里面。拖着走,不到200公尺,走一小段堑壕,又攀悬崖峭壁,晚7点钟拖到"147”,陈光辉说,别走了,你太可怜了。明天再走吧。这时阵地都换防了。步兵三团接防。 第二天早晨5点钟天不亮,我和陈副营长连拖带拉走四个小时到“208”。 我浑身是泥浆,王兴辉赶快倒水给我洗。他高兴了,不让我说话。浇完之后没衣服,通信股长给我一件背心,一件裤头。我不能老是坐着,我要走路,刚一抬脚,迈第一步,第二步还没抬脚,一下子跌倒地下,再也起不来了,又弄一身泥巴。团长扶着我又冲,团长警卫员又给我换衣服,架到团长铺上。9点钟李副师长来到团里,我们相识后,第二次握手了,他那粗壮有力的大手,紧紧攥着我的手不放,严肃刚强的目光中闪动了晶莹的东西。 郑师长派车把我接到师里。 北京“212”吉普飞驰M洞,师长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下车,走向师指挥所,师长老远迎过来,老远把我抱住。边拍着我的肩膀,边说: “哎哟,我的英雄,你可下来了……” 当天晚上,M洞举行宴会,为我接风洗尘。薛主任代表全师官兵敬酒…… 我激动了。我举起那白色的玻璃高脚杯,我说:各位首长,各位领导,同志们。感谢你们。感谢为祖国为人民而阵亡的战友们,这杯酒我不能喝,应该给他们——我把酒洒在M洞,洒在祖国的土地上。 我哭了,我第三次掉泪了!
政委捎来一个“吻”
仲宫,大礼堂内。 年轻的军官们在听中将讲课。中将声音高吭嘹亮,左手卡腰,右手不时地挥动。他在讲学习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必须把握的几个问题。旁证博引;谈从海湾战争看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理论的发展。像是在战场上作动员,把年轻的军官们吸引住了。 中将刚从国防大学深造归来。在同期学员中是年纪最轻,军衔最高的。JZM主席几次和国防大学学员座谈,都是他第一个发言。国防大学研究所姚延进所长在讲课中一直表扬中将的刻苦学习精神,今天中将的讲课以海湾战争为背景,讲未来战争超立体,空中作战的独立性,电子大战,机动大战,消耗损失大战,隐形大战,把我们慑服了。 我突然想起那场边境战争,中将那时是军政治委员。当时的作战处长现任某师师长冯育军不只一次向我推荐写写他。冯师长说中将更适合作一名军事指挥员,说他对战场判断的准确性,宣传鼓动,临阵动员有极大的煽动力,战士们听他一吆喝,把手一挥就冲上去了。他完全是我党我军一手培养起来的军事政治指挥员。他从小很苦,诞生在胶东的一个渔民小村,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上学也不多,至今字写得也不好。曾打下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空中战斗英雄张积慧,说起他也非常佩服。让我把历史的时针倒拨到八年前。作为军政治委员的他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笔者在冯师长保存的录相资料中看到,那时的军政委一头长发,胡子拉碴的。身体瘦削,手拄一根木棍,在泥泞的阵地上跋涉。那时的政委分析和认识了战场处于热带山岳从林地,“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雨季阴雨连绵,洪水泛滥;旱季浓雾茫茫,视度不良;敌我阵地紧贴,有的哨位语声相闻,星火可见。在军作战会议上,政委提出战时抓基层要抓到猫耳洞。有部分同志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是连长指导员的事。政委说,猫耳洞是战士生活、战斗的地方,是战士的家,两干多个猫耳洞组成了坚强的一线防御外壳。猫耳洞里的战士日夜经受着苦累的煎熬,时刻面临着生死的考验。政委激动了。“5.3l”之战,我部正式接防的第二天,就抗击了敌人加强团规模的进攻,取得了歼敌XXX余名的胜利,但这次战斗也暴露了问题就是丢了两个哨位,两个猫耳洞,“7.19”之战,敌又以近一个团的兵力,采取先偷袭后强攻的手段,分三路向我前沿阵地实施轮番攻击。敌始终未能攻入我阵地。尤其难忘的是,我一个阵地的6号哨位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两次出现只剩下一个战士带伤坚守的情况。战士韦昌进在哨位被炸塌,自己负重伤的情况下,孤身奋战群敌,一人坚守哨位十几个小时。他以自己英勇壮举,保住了哨位,保证了寸土不丢,我们在作战室都为这样的英雄而感动。 政委一席话感染了在场的师团领导。政委站起来,左手卡腰,右手按在作战案板上,停了停说,同志们,军党委研究决定,我们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步入猫耳洞,走到战士中,军委、总部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坚守阵地,长期作战;赋予我们的任务是攻必克,守必固,寸土不丢,不断给敌人施加压力。这场战争,既是军事仗,又是政治、外交仗,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军长站起来了,他身材魁梧,说话有力,抑扬顿挫。他说,同志们,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必须准确精细地摸清敌情和地形、反复听取基层战士的意见,研究战斗方案,确保决策和决心正确无误。政委的话我完全同意。今天会就到这里,没有什么好送给你们的。我想了四句话送给大家。“八级沙盘同切磋,民主会商制敌策;三方六出齐努力,仗仗定能奏凯歌”。 冯师长给我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有一天,政委去条件最艰苦的N口方向。当他柱着木棍跋涉在没膝深的泥浆里,来到前沿阵地时,碰到师政委正满身泥水地从猫耳洞里钻出来。政委看到师机关组成的二十多人的军工队正向阵地上背工字钢,为战士们加修工事的情景。军政委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战士们也拉着军政委的手激动地说,这是领导和机关帮我们建“家”啊! 师政委向军政委汇报。 这里原来是一个长不到三米,宽仅有一米,高只有七十厘米的石洞。战士张远祥、李树水和徐书铎三人就战斗和生活在这里。他们三个整天蜷曲在洞内,伸不直腰,抬不起头,大雨频下,洞内积水,热气蒸腾,蚊虫叮咬,全身的皮肤大部分溃烂了,衣服已成为多余,用不着遮盖,这里是男性王国。四千年前的古希腊人以美丽的人体显示斗士的英武与俊美,从此有了裸体雕塑,有了罗丹和米开朗琪罗这些艺术大师,以及维纳斯、大卫、自由女神……而在这里,是生活将这三位战士塑成为三尊裸体雕塑。 他们三个只知道送走白昼,又迎来了黑夜,但不知生活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们只是互相看到战友的头发长了,胡子也长了。梯恩梯的气流和横飞的钢铁破坏了生态平衡,也改变着生物的生活习性。大个儿的蚊子,飞机般地在猫耳洞内盘旋,伺机吸吮战士的血;大个儿的老鼠饿极了,不仅抢食压缩饼干,竟然能咬掉战士的脚趾。不知《诗经》里描写的硕鼠究竟有多大,阵地上的老鼠大如猫。 这是一个平静的夜,张远祥、李树水和徐书铎都睡去了。朦胧中他们发现好像多了一个人的呼吸,又感到一种凉森森的物体贴在他们身上。点燃蜡烛一看,啊!三人同时惊出一身冷汗——原来一条碗口粗的蟒蛇睡在他们身边。三个北方籍战士惊恐地跳出洞口。当再次进洞看它时,只见它闭目合睛,安祥得像人一样。它睁开了眼,发现了人,却没有伤人,那眼睛里似乎没有恶意,它懒懒地走了。蟒蛇走了,三位战士的心豁然闪出一种思考:世上的动物相中的地方,不也是人的生命有希望的地方吗?于是,他们反倒天天盼那大虫再次回来。那大虫果然回来过,它与人依然和睦相处。 生活如此苦,而战士的内心是那样充实。战斗间隙里他们看着飘动的云雾和天上的星星月亮,谈吐心曲。他们思念家乡和亲人;他们谈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们认为:“人生在世,能够到南疆来,也不枉作八十年代的一个青年。”他们想到:“如果一旦死去,还没有尝够人间的甜密。”他们坦白地说,他们不愿死,但见到那么多的同志“光荣”地去了,死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次战斗中,有颗炮**弹炸在洞口,一块弹片击中了徐书铎的头部。张远祥和李树水把奄奄一息的徐书铎抬回洞内,知道他们这位朝夕相处的生死战友很快要谢别人世了。李树水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说:“书铎,我的好弟弟,你醒醒,有什么话你快说啊!” 徐书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见他抬起无力的右手,指了指洞内的一侧石缝,张了张嘴便咽气了。悲痛万分的李树水轻轻地放下了烈士的遗体,从烈士手指的石缝里取出他给父母写下的遗书。他声泪俱下地念道: 娘,我已经不是在家的书铎了,虽然我只有十七岁,但我已是一个战士了。在战场上,战士不分岁数大小,都要担起保卫祖国的使命。初上阵地,我是怕死了再也见不到娘你了。现在我不怕了,两位战友很勇敢,我不能当草包。儿十分想念娘,梦中不知见过娘多少次。我也总是想带着军功章回到你的面前。可是我已经作好了只在世上度过十七个春秋的准备。真要那样,望娘不要难过。儿是准备活着回去见你的。 …… 后来,军政委拄着棍子跑了前沿几十个猫耳洞。回来后总是说,看看战士蹲的猫耳洞,再听听他们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战士太可爱,太伟大了!每去一次猫耳洞,每当看到战士们为祖国奋勇拼杀的高尚行为,我的心情都难已平静。他们的索取是何等的少,而奉献又是何等的大,我禁不住问自己与战士相比,我差得有多远?有一次,政委从阵地上下来后,写了这样几句诗。他自己说,是打油诗,但表达了他的真实思想情感。 艰难困苦,流血牺牲, 净化了我的心灵; 更爱祖国,爱人民, 爱我的士兵。 莫叹人生短, 只求多贡献; 虚度一百岁, 临终也遗憾。 …… 这是南疆阵地上那个不起眼的除夕之夜。 春节,是战线两侧人民同庆的传统节日。没有任何人组织,没有长官下令,是双方士兵节日情感的流动,几乎在同一时刻,阵地上升起了红、黄、白三色信号弹,接着便响起了枪声,枪弹带着色彩斑斓的曳光向上空飞去。一刹时,仿佛是所有的阵地都响起了枪声。这不是战斗,双方的子弹都向天空奋飞,犹如“起火”、“二踢脚”、“钻天猴”。此刻战区的夜是一个彩色的夜。少项,对方阵地与我方阵地上空又升起了数十枚照明弹。一方是白色的,一方是红色的,仿佛是一颗颗明亮的天灯,由一朵朵花色小伞吊着在空中游荡。它们超越了国界,像一群凌空飞翔的鸟儿…… 这时的双方士兵忘却战争,记起了对故乡的思念。他们从掩体里,从大小猫耳洞里,从往日不敢露面的地方涌出来,狂呼着,歌唱着,欢呼这个生命的自由时刻。 年三十那天,有两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和军工一起登上了L山战场的最高点——被称之为八十年代上甘岭的某高地,同战士们一起欢度新春佳节,他们是张军长和佟副军长。 现在已经是成都军区中将政委的张军长,回忆这一段时,他说这是今生最难忘的春节。 在某高地的另一方。 军作战值班室里,军政委正伏案疾书。他聚精会神,洋洋洒硒千言的慰问信写成了。就在他快要停笔的时候,忽然热血沸腾,他想起了那个情景,那个猫耳洞—— 那个奇袭十六分钟就夺回来的神秘哨所,原来是一个天然石缝,只能容纳三个人。每次去一个小组,还有一人半边身子在外,前后不到半个月,从一团换到三团,先后好几个连队换了一茬又一茬。那里根本就不是个哨所,是个易攻难守的小石缝,人在那里别说打仗,就是平常也难已生存。忽然有个胶东人,并不是山东大汉,个儿不高,黑乎乎的脸膛,笑时还露出小虎牙。他叫张传江,某团二连排长。政委来到他的阵地,他向政委拍了胸脯,他要守那个哨位,保证两个月不下来。他还和政委套近乎,说是政委老乡,生在荣城一个小渔村,从小喜欢下大海。他知道政委铁面无私,有个老乡想开政委的后门,参加突击队,政委没答应;他说他这个老乡开后门是为各级首长排忧解难的。政委听了他的设想,当即拍板,好,你去坚守两个月,把天然石缝弄成容纳一个班的猫耳洞,阵地还要造得像个样,到春节我亲自给你写信,下阵地时我给你接风。 果然,张传江不负厚望。他带了两个士兵,还带上小锤,钢钎,雨**管,炸药,工字钢。在石缝里今天敲一块,明天炸一块,发扬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的精神,果然把天然石缝改造成一个猫耳洞。对方起初一天三次两番来骚扰。后来听到那地方响声不断,不知我军弄啥新式武器,再也不敢露头了。猫耳洞真的能容纳一个班了。煤油炉,小铝锅也能烧饭煮吃的了。四个人可以坐下来打扑克,一人站哨其他人可以睡觉。洞前修的像个小花园,有罐头盒里栽的杜鹃、石兰、鸡冠花,洞门两旁栽上草坪,上面用石头摆成对联: 有我英雄将士在,敌军休想度边关。横批:气贯长虹。 上端有一个观察哨,敌人不敢袭击,也不敢炮击。据说后期对方是没有炮**弹,还是彻底折服了,不得而知,反正张传江得了意,他用带在身边的傻瓜相机照了十几张照片,寄给了老乡政委。 政委也没有让他失望,在信的末尾写了一句在当时来说,非常时髦,非常亲切的话。连夜派人送到猫耳洞,张传江看了信,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笔者去找已经当上营教导员的张传江。他从包袱里取出那封热情洋溢的信。仍然视如珍宝,他不让摘抄,不让传录,只是露出他那小虎牙嘻嘻笑着说:你瞧,你瞧,政委说,请捎给全体同志们一个亲切的“吻!”

 Post By:2011/1/31 18:11:41
Post By:2011/1/31 18:11:41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1/1/31 22:01:39
Post By:2011/1/31 22:01:39




 Post By:2011/2/1 9:25:37
Post By:2011/2/1 9:25:37




 Post By:2011/2/1 12:18:02
Post By:2011/2/1 12:18:02




 Post By:2011/2/4 0:11:11
Post By:2011/2/4 0:11:11




 Post By:2011/3/1 11:23:41
Post By:2011/3/1 11:23:41




 Post By:2011/3/1 11:31:10
Post By:2011/3/1 11:3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