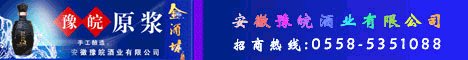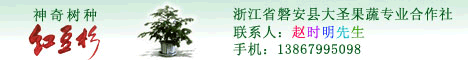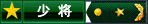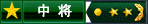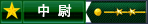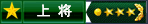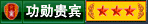第—章 上校军官
接上篇
骡马化时代
我们那拨儿兵是在骡马化时代步入军营的。那时的团长营长都有匹战马,白色的,黑色的,棕色的,花白色的,枣红色的,马“咴咴”的叫,兵也嗷嗷的叫。那时日常用千军万马战犹酣来形容野战军的豪壮,就连机枪连、炮连都有马和骡子。行军路上我们步兵都自觉往路边站,让马和骡子在兵营里和兵一样荣耀,它们也和兵一样服役,报效祖国。战马立下战功将终生不退伍,死后将忠骨埋入烈士陵园,树碑立传。和平时期的骡马生活和兵一样艰苦,一天有四毛钱的豆饼补养。有人开玩笑说,炮连机枪连的伙食最好,因为他们可以扣骡马的军饷啊!其实人和马在一起时间长了,感情甚笃,有的兵还掏腰包买东西给马吃呢,这时候骡马就会眼含热泪瞧着你。
我一当兵就给团长的那匹枣红马添草加料。传说团长在朝鲜战场和美国鬼子打仗,一个连打没了,就剩他自己了,出于满腔怒火,他把投降的敌人也打死了,受了处分,不然早当师长了。团长喜欢战马,这年春天带我去黄河三角洲相马。我有幸目睹当时全军有名的军马场“十姐妹”风姿。她们一个个飒爽英姿,手拿套杆飞身上马,然后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那真叫雄壮。后来我经常梦见马场“十姐妹”,那辽阔无垠的大草原,那浩如云海的战马群,一想起来我就热血沸腾。
我们那一拨儿兵,是坐着闷罐儿车到的。那是个雪花如絮的冬季,铁路两旁雪深齐膝,漫山遍野白雪皑皑,沟沟壑壑都填平了。兵们穿着棉衣棉裤,小帆布外罩,棉帽有紫色毛的,也有绿色毛的,我领的就是一顶绿色的。后来老兵复员时,我宁愿换一顶旧帽也不要那绿色毛的。我们背着背包、挎包从闷罐车的车厢里迷迷糊糊的下来了,像赶羊似的。
天蒙蒙亮。雪后天寒,风呼呼叫像刀子似的割耳朵,兵们集中的路基下,一块平坦积雪的场地上。一个个缩头袖手坐在背包上,风刮得透心凉。只见一个大个子军官,戴着红领章红帽徽,黑红的脸膛,训斥连长:他XX的,这样坐着不冻死啊!起来,都起来,跑步,不跑五公里别吃早饭。军官严厉得像关公,手卡着腰,站在胶济铁路上,看着兵们顺着铁路线跑,跑啊,跑啊,那时我认为五公里有一百里路长,肚子又饿,饥肠辘辘两眼冒火,肺要爆炸似的,心想,这个官怎么这么狠啦!他每天早晨带着我们出操跑步,顶着风雪练嗓子,站在河边使劲地吼,迎着西北风使劲地喊口令。他也在吼,他吼什么呢?他吼: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别人听不懂,我懂,我略知诗词。时间长了,觉着他和蔼可亲。他说,小伙子们,兵不练不行,这样的身子骨,怎么和敌人拼刺刀哇!他是我们的副营长,后来听说他在朝鲜战场一枪挑死两个美国佬。
当兵前见过电影上的八路军、解放军,只知道扛枪打仗,压根儿不知当兵的怎么过日子。新兵一入伍,第一课就是为人民服务,谈入伍动机。有个兵说,俺听说部队上天天吃油条,心想当兵有油条吃,就来了。谁知新兵肚子空,没油水,新兵连粮食不够吃,炊事班就煮稀饭喝。我们那个班一顿要吃两水筲稀饭,还觉不饱,再去打,炊事班已经刷完锅了。
那时的兵,光搞突出政治、思想第一,兵不大怎么训练,有的当了几年兵开了几年山洞,盖了几年房子,啥武艺没学着。当兵不习武,就会出事故。
我们连也出了个熊包,那是我的同乡大耳朵。新兵来了不到三天,老家的县社队三级妇女主任就来了,说是大耳朵在家时和军人未婚妻有不正当关系,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了。那兵回来问是谁的?姑娘说是大耳朵的,可这时大耳朵已经飞驰在胶济线上了。妇女主任们责无旁贷紧追慢赶来了,要把大耳朵带回去。我的天啦,大耳朵现在也是解放军一员了,我们早就听说,从当兵那天起,名字就上了总参谋部了,哪能随便带走呢。
妇女主任们临走时,我和几个同乡送她们上火车。我在车上说,把那个女的给大耳朵不就结了,反正都是军人。县妇女主任说,是谁的就是谁的,不是谁的就不是谁的,军婚是不能混淆的,婚姻法上保护军婚。那时我们就放心了,当兵的媳妇没有人敢碰。这一想火车哞地一声开了,我们几个新兵请了半个小时假啊。车到下一个小站,跳下车没命地跑,归队还超过一分钟。排长就点名说,《南征北战》电影上我军和敌军抢占山头,就差那么一分钟,我军上去了,把敌人打下去了。
大耳朵觉得给同乡丢了脸,拼命干想立功赎过。他在炮连放马,一天晚上起大风,忽然马棚失火,大耳朵英勇打火,棉袄都烧穿了,连长给大耳朵口头嘉奖一次,那时我们认为连长口头嘉奖就是英雄了,都觉得大耳朵给同乡争了光。不久搞斗私批修,大耳朵说火是他自己放的,大耳朵被关了禁闭,新帐老帐一块算,除名遣送回家了。我还写了批判稿:玩火者必自焚。
在新兵连安微兵和江苏兵对着干,都想起早抢大扫帚,江苏兵就编了谣儿笑话说我们:“从肥东到肥西,安徽买个老母鸡,拿到河里洗一洗,除了骨头都是皮。”安徽兵口笨,老实,没有江苏兵精,仍然每天闻鸡起舞,扫地不止。
有一次一个安徽兵和江苏兵同时起床,都抢一把扫帚。一太早安徽兵就给排长告状,说江苏兵耍流氓。一问,原来那江苏兵说,“安徽姑娘辫子长,牛屎巴巴糊墙上”。排长把眼一瞪,找你班长去,乱弹琴。后来我们觉着不对劲儿,江苏兵哪能知道安徽的事呢,一琢磨只有排长到安徽去带过兵,原来排长也是江苏的。
我们连长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人不苟言笑,那时他才二十多岁,我们都以为他是四十岁的人了,见到连长如老鼠见猫也。有一次帮厨,炊事班长是个老兵,山东聊城人,小个儿小头,爱开玩笑,别人开他玩笑也不恼,老兵都叫他小脑袋。这时厨房外来了一个小姑娘,人长得细皮嫩肉,小巧玲珑,穿着月白色衫儿,一条黄军裤,脸蛋啥模样儿,我们不敢瞧,只见一条十分悠长的黑辫子打到腰际。小脑袋班长说,哟,连长闺女来啦。那闺女也跟班长开玩笑,让他称面儿把秤杆儿高一点,说小脑袋班长脑瓜灵,粮食还扣秤。班长说,哟嗬,昨儿晚上连长没让你吃饱昨着?那小姑娘反击道:小毛孩儿,鸟儿还没长全呢?知道个啥?那时的新兵傻儿呱唧的,并不知道其中意境。姑娘走后,班长说,当兵的他XX的就这德性,一顿撑死,一年饿煞。当兵的也爱美啊。别看连长严肃,人家给他说的对象家有姐妹两个,说的是那个大的,回家一相,大的不如小的漂亮,可人家小的正在上学呢,连长就等着,一等等到小三十了,今年才完的婚啦。你们看那姑娘俊不俊,水灵不水灵,我要有这么个老婆,死也心甘情愿。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那是连长爱人,并不是闺女。
小脑袋班长嗓子很亮,人长得也精干,是连队演唱组骨干。那时普及革命样板戏,部队没有营房还住乡村。军民联排《沙家浜》,大队妇女主任演阿庆嫂,小脑袋班长演刁德一,效果很好,每场演出都有掌声。后来,小脑袋班长复员了,不久,又悄儿没声的回来了。原来当兵不许在当地找对象,他就来了个“迂回”战术,给大队妇女主任做了倒插门女婿。
……
上述的故事,现在想起来觉得好笑,但当时真是这样的。我家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从小没见过火车,头次坐上军列,十分亢奋,可是在车上听城里兵说闷罐车是运牲畜的。当时我们新兵从火车上下来一看,那列闷罐就后头这两节车厢下来我们一拨儿兵。在黎明前的晨光里,前面车厢没有一丝动静,心想那里面装的牛羊吗?忽然“哞”的一声吼叫,列车冒着烟雾,缓缓向前开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胶济线长着啦! ……
当兵主旋律
胶济线上的列车滚过多少个轮回……
兵营里的士兵走过多少青春……
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当兵的离家前一天,都不知道当兵干什么?但村头小河边,码头车站上,有一个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当兵人傻乎乎的没想到的事,姑娘想到了……
战争突然降临,开进大约在春季。
胶济线上沸腾了。过了三十多年和平生活的将士们没有慌忙,好像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向演兵场告别,抖一抖征衣,来到广阔的军用机场。一架架银燕停留在停机坪上,整装待命,那些农民的儿子们要凌空翱翔……
这里的出征不是古远那“车辚辚、马箫箫”的壮观,当涡轮机的轰鸣划破长空时,机场上的将军们招手,茅屋瓦舍有亲人们泪眼仰视翱翔的机群,他们飞过祖国的山河,顿觉胸怀无比博大……
在世界空运史上,英国人在世界第一次大战的1916年,对固守待援的部队空运物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941年,德国在克里特岛实施空降作战;动用530架飞机空降750名敢死队和一万名空降兵去完成作战任务;在现代战争中,美国给远在11900公里外的以色列空运武器、弹药和坦克27895吨;海湾战争,充分表明多国部队强大的空运水平。第一次将全副武装的数干名军人运抵疆场,这也是我军空运史上的壮举。
当先遣营的机群一架架射向蓝天后,胶济线上的一个个军列满载着参战的军人,车辆、火炮准备登程。战争,牵动着千家万户,来队探望的士兵亲人们已经离去,小站上很静。士兵的脸上凝满豪气和庄严,这是一次血与火的严格考验。战争,打破了生活的宁静,加快了生活节奏,出征命令一下,数百封催归的电报发给探亲、休假的军官与士兵,山山岭岭,平原大川的瓦房草舍里出现一幅幅壮别的动人场面——
山东乐陵县,战士刘福禄回家完婚。电报到时也是吉日到时,父亲瞒下催儿归队的电报,婚宴散尽,洞房花烛,蜜月第一天清晨,父亲将电报交给儿子。刘福禄看着,叫一声妻子,道一声父母:“电报来催,部队有事,我必须马上回去!”他就这样别家归队了。
在湖北的一个小山镇,这里有志愿兵潘三华的家。潘三华到家尚未坐下,一封电报落在他的手中,他二话不说,吃了碗亲人做的面条儿,推开竹栅栏,登上归程。
一位班长,回家看望重病的母亲。接到电报,跪在母亲床前说:“为儿不孝,可儿是为国,请妈妈原谅我吧!”说罢挥泪而归。他在战场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脚,在八百米生死线上爬了八个小时,终于爬上了阵地,他跪在苍天下,向远方的母亲叩了一个头,然后倒在了战友怀中……
一位大学生排长,将与同系的婷婷玉女结为秦晋之好。他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电报步入校门,女友带着几分哀伤几分幽怨目视他说,难道你就没有其他选择了,你就不为我想想吗?他说,部队来电,我马上就走。女友抹了眼泪,说:“好,我祝福你——”橄榄枝掉在地上,电报他揣上了征途。
一位在微山湖畔长大的连长,接到催归的电报,来不及通知上街赶集的妻子,留下一张纸条,道:“电报急催我归队,来不及辞别,我留条于你,孩子锁在屋内,我走了!日后回来,我负荆请罪……”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
军列的汽笛声打破了夜的沉寂,车轮载着沉重的负荷慢慢地启动,钢轨下的大地微微颤抖,将士们就要走了,从此开始了他们各自命运的新征程。他们带着前辈的赫赫战功,怀着崇敬的英雄形象,带着这支部队在华北平原和三八线上的赫赫威名,带着诞生于五千年历史中的传统血骨走了!
这是一个美好的春夜,车轮滚滚向前时,一个探身车窗外的军人,向西山之巅的一位年轻母亲的剪影挥手告别;车轮滚滚向前时,一位战士的父亲和妹妹呼唤“孩子”、“哥哥”,冲破木条子门奔向列车,扑倒在地……
车轮滚向前时,薛朝应爱妻陈守玉,因为车间忙,来队晚了,这位泼辣大方,贤惠善良的南国淑女,果断决定停在小站,她一手拉着儿子,一手把家里带给丈夫的合肥烟、渡江烟、安徽糕点、糖果……一古脑地塞进闷罐车厢里。士兵们挥动着军帽,高呼:“嫂子乌拉!“嫂子万岁!”……
军列远去了,远去了。陈守玉没有流泪,只是微笑,抬头遥望湛蓝湛蓝的天空,一群大雁从南方飞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23 18:06:26编辑过]

 Post By:2011/1/23 18:02:33
Post By:2011/1/23 18:02:33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1/1/23 18:46:38
Post By:2011/1/23 18:46:38


 Post By:2011/1/23 22:10:02
Post By:2011/1/23 22:10:02




 Post By:2011/1/23 23:02:19
Post By:2011/1/23 23:02:19


 Post By:2011/1/23 23:46:10
Post By:2011/1/23 23:46:10




 Post By:2011/1/24 12:33:22
Post By:2011/1/24 12:33:22


 Post By:2011/1/24 12:34:22
Post By:2011/1/24 12:34:22


 Post By:2011/1/25 9:33:56
Post By:2011/1/25 9:33:56




 Post By:2011/1/25 19:49:51
Post By:2011/1/25 19:49:51




 Post By:2011/1/26 15:43:29
Post By:2011/1/26 15:4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