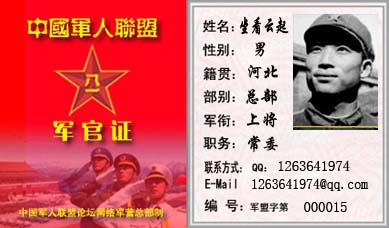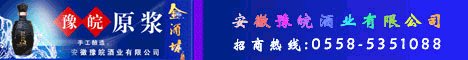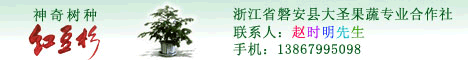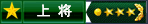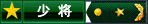给我一门炮!
远处炮声隆隆,海浪翻滚。
我在阵地的堑壕里探头向海的方向张望,一只手从背后按住我的头。那手劲不重,却挺执拗,带着不容置辩的力量。我转过脸,是位头戴钢盔、脸色坳黑的娃娃相的新兵。
“这太危险了,你快下来。”
“我观察一下情况,马上就完。”
“不行,敌人随时都会开火。”他指着后面两米处的一个新鲜的弹坑,“喏,你看,这里昨天还落发炮**弹呢!”
“我只看一会儿。”我缠住他苦苦商求。他心软了,使劲眨巴着一双挺好看的大眼睛:“那……”
我兴奋地转过身去,一顶钢盔扣到了我的头上……
“你怕不?”我侧过身来问他。
“生命只有一次,怎么不怕?可他们要闹独立,怕顶什么用?维护祖国统一,捍卫领土完整,只有打!我是到这里尽义务来的,就是在这里流尽最后一滴血,掉在海里喂鲨鱼,也算是尽义务……”他脸上显示出与那副娃娃相很不相称的严肃。
“你多大了?”
“十八。”他一笑露出两虎牙。
“我不信。” “呵呵,我虚报一岁来当的兵。”
“一岁?至少两岁!”身边的战友故意唬他“他的嘴上还没有长毛哩!”
哈哈……
连长匆忙跑过来,站在我不远的位置。“同志们!这是关键的一战,一会儿五连的兄弟就来支援咱们,咱们一定打个漂亮仗,打到对面去……”连长的喉咙显得有些嘶哑。
我仔细看看,一公里的堑壕里,全是四连的官兵。一些伤员正在后撤,重伤员抬在担架上,轻伤员拄着棍子,或是互相搀扶着,血迹斑斑和撕烂的军装粘贴在身上,一个个像从血水中滚过似的。
见五连的战友来增援,堑壕里的伤员主动让开,有的喊“打”,“上啊”,有的还在担架上挥动拳头。 看着身边的一具具烈士遗体,有的血肉模糊,有的残缺不全……我想哭,没有泪,想吼,吼不出来…… 营长刘春阳跑过来,两个通信员提着一个白色的塑料桶。营长站在沙地上:“同志们,发起总攻的号角就要吹响了,我来给大家壮行。是男人的,拿出碗或牙缸,把酒倒上……”
战士们一只手拿着武器,一只拿着牙缸、铁碗……通信员一一倒满。
“英雄们!好汉们!”营长“嚯”地立正,挥把热泪:“我代表二营,敬你们一杯……”
战友们的铁碗、玻璃杯和牙缸,“叮叮当当”碰在一起……
泪和酒,顺着汉子的鼻翼和嘴流着,淌着……
“你曾经也是一名军人,来,你也干了……!”营长,端着牙缸,冲着我说。
我擎起酒杯,酒溢出来了。 眼前模模糊糊的,一会儿是身边的战友,一会儿是我远在西南的妻儿……
“在边防穿了十多年军装的我还算不得军人,起码算不得真正的军人。今天,不!就在刚才,看着祖国的疆土,望着蔚蓝色的海洋,我感到再一次入伍了——就在那时,一名新兵从背后给我戴了顶钢盔……,我不能代表谁,只代表我,我的妻子和孩子——这样一个受你们保护着的幸福小家庭,敬你们一杯……”
我一饮而尽——整整一牙缸绿色琼浆。
泪水从眼睛和鼻腔里冲涌而出。
“给我一支枪,加入到你们的行动中!”我说。
“不!我当过炮兵——给我一门炮!”我喊。
“他娘的,我打到对面去!”我吼着。
……
“喂,你在吼什么?给你什么炮啊?”我感到有人在推我,还在说话。
我挣开眼睛,看看四周。原来自己还躺在床上。
“该出操了。咦,你哭了?是不是做什么梦了?”战友关切地问。
“没什么?”我穿衣而起,走到窗前,极力地望着海的方向……
[此贴子已经被梦断思飞雪于2010-7-30 23:45:06编辑过]

 Post By:2010/7/30 23:27:55
Post By:2010/7/30 23:27:55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10/7/30 23:38:52
Post By:2010/7/30 23:38: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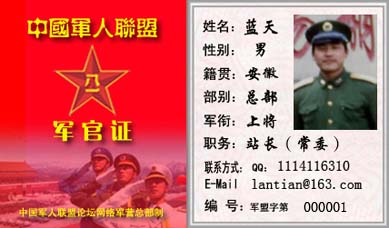


 Post By:2010/7/31 0:22:35
Post By:2010/7/31 0:22:35


 Post By:2010/7/31 8:22:09
Post By:2010/7/31 8:22:09




 Post By:2010/7/31 11:41:30
Post By:2010/7/31 11:41:30




 Post By:2010/7/31 11:43:30
Post By:2010/7/31 11:4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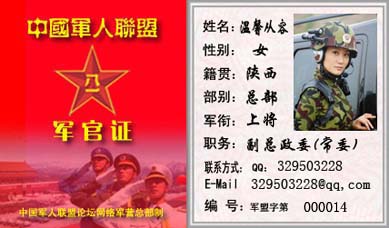


 Post By:2010/7/31 12:54:46
Post By:2010/7/31 12:54:46




 Post By:2010/7/31 13:23:06
Post By:2010/7/31 13:23:06




 Post By:2010/7/31 13:27:24
Post By:2010/7/31 13:27:24




 Post By:2010/7/31 15:18:23
Post By:2010/7/31 15:1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