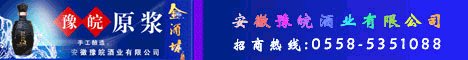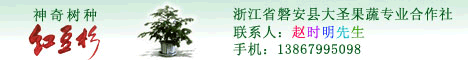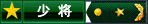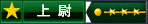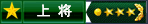这里是风雪弥漫的“寒极”世界,这里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六月雪花飘,四季穿棉袄”的“生命禁区”。一些中外探险家的在此失踪,更为这里染上了一层神秘、恐怖的色彩。然而,在这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雪山脚下,却奇迹般地生存着一个“女人村”。
丈夫在喀喇昆仑山、阿里高原、帕米尔高原无人区的雪域边关守防,妻子随军到了雪山脚下,名曰“随军家属”。可她们的住地距边防近则几百公里,远则上千公里,她们随军却不能随队,仍然长年累月地与丈夫“牛郎织女”,天各一方。时间久了,人们把这里称为“女人村”。
“湘妹子”高金玉坐半个月的车来到边关与心上人团聚,待赶到部队留守处却大吃一惊:离他还有一千多公里……
昆仑8月雪纷飞。一辆军绿色的东风牌卡车行驶在耸入云端的新藏线上,驾驶室里,坐着一位年轻的少妇。汽车翻越一座座冰大坂,车速已经快得不能再快了,可少妇还嫌慢。她叫高金玉,是阿里军分区日土县武装部参谋何正良的妻子。
三天前,武装部驾驶员送人下山,路过叶城,告诉她何参谋在乡里训练民兵时得了重感冒,烧得厉害,虽打针、吃药、吊水,但高烧仍没有退。
“妻子的心系在丈夫身上。”高金玉也一样。1982年,她与当时在阿里边防当排长的何正良在湖南水乡喜结良缘,婚后夫妻俩鸿雁传书,相亲相爱。女儿出生后,她赶忙托人给丈夫发加急电报报喜,谁知道孩子满月后收到丈夫的电报,上写:“生了没有?”小高很伤心,显然,那封发出去一个多月的电报,他还没有收到。事实上,丈夫所在的那个“雪海孤岛”,与外界联系相当困难,尤其是遇到大雪封山,即使十万火急的电报,也要等到来年夏天封山期过了才能收到;平时通信也很困难,接到的信常是前后颠倒,让人心里惦记得不行;每次探亲,光来回路途就要折腾一个来月。
高金玉左思右想,决定随军,好歹离丈夫近一点。于是,她第一次上了边关。她带着四岁的女儿,一路上经过半个月的颠簸,总算来到了昆仑山下的部队留守处。她想,这下总能与正良见面了吧!不料,等到天黑仍不见他来。一问,她才知道,“大本营”距丈夫守防的哨卡还有一千多公里的高原路……她惊呆了。
从那时起,高金玉的一颗心被丈夫拽拉着,魂牵梦绕在风雪高原。每当丈夫一走,她就提着心过日子,生怕他在冰天雪地里有什么闪失。一次,她听说有个老兵查线遇到暴风雪时活活冻死在雪地里。当时,她狠着心,逼何正良写转业报告——她实在受不了那份日夜为丈夫担惊受怕的罪呀!可何正良却说:“咳,我怎么好意思给领导说‘山上太苦、太危险,我不干了’。一个大男人,说这话张不开口哇!”从此,她再也没有提及转业的事儿,只是以百倍的柔情关心着丈夫:每年都给丈夫织一件厚厚的新毛衣;一有军车上山,就给丈夫捎一些他爱吃的水果和人参蜂王浆一类的补品;每当丈夫带着一脸乌紫下山休假,她都心疼地下令:“好好歇着,什么活也不许干……”
如今,丈夫在山上害了病,高金玉心里不由得一阵阵紧缩。她当即闪出一个念头:上山看看正良去。
左邻右舍的姐妹们听说高金玉要上山,都赶来劝阻。那毕竟不是女人去的地方呀!
高金玉的犟劲上来了,她不信这个邪,非要领教领教“生命禁区”的厉害不可。她连夜宰了两只鸡,第二天又到县城买了些治重感冒的药和几提兜苹果。七岁的小女儿听说杏仁能治拉肚子,也找来了一筐杏核,用小铁锤砸呀砸呀,砸了一百颗杏仁,嘱咐妈妈一定要捎给爸爸。
这是高金玉第一次上高原。
汽车翻越五千多米的麻扎大坂时,强烈的高山反应使高金玉头痛欲裂,胸闷气短,最后一个劲地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那滋味真是欲生不能、求死不得呀。
驾驶员好几次问高金玉:“你还上不上?”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就是死了,也要上山!”行至多玛兵站,不巧大雪封住了通往日土的五十多公里的山路。这位湘妹子死活不听别人劝告,坚信曾在书里看到的那句话——路是人踩出来的。她独自一人到积雪中“踩路”去了。兵站人员赶忙给日土武装部打电话。当何正良风风火火地领着人赶来时,高金玉的身后长长地拖着一条歪歪扭扭的“雪路”。
|
在日土,高金玉呆了一个月。她每天精心照料丈夫的起居饮食,陪他散步、看电视,给他讲山下的
故事和女儿的可爱。也许是因为妻子的到来,何正良很快痊愈,并投入了工作。高金玉下山时,夫妻俩在班公湖畔依依惜别。她对他说:“你等着,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千苦万苦,没有氧气吃最苦;千难万难,在高原上培养孩子最难。”期末,孩子考试仅仅得了二十七分,竟是全班第一名。守防的爸爸回家的时候,就是孩子们最
幸福的日子……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对女人来说,是一生最痛苦,也是最需要丈夫关怀的时候。阎丽躺在产床上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抱着怀中啼哭的婴儿,眼里噙满了泪水。此刻,她多么希望丈夫贾双宏能在身边端茶倒水啊!然而,当在卡拉其古边防连的丈夫打来电话,询问是否需要请假下山侍候她的时候,深明大义的她却回绝说:“左邻右舍的姐妹把我关照得很好,你就安心工作吧!”阎丽知道,哨卡指导员探亲还没有归队,丈夫作为一连之长,全连
官兵比她更需要他。
有了孩子后,意想不到的困难摆在阎丽面前:一个人既要拉扯孩子,又要上班;每天下班回来,房子里空荡荡、冷冰冰的,第一件事就是劈柴生火做饭,有好多次她的手打起了血泡,委屈的泪水打湿了她的面颊;她在干家务的时候,孩子几次从床上摔下来,有一次摔得头破血流,她心疼极了,却又无可奈何。
一天夜里,孩子患重感冒,咳嗽、高烧,她也病倒了,浑身无力,头痛难忍。深更半夜的,一个女人家到哪里去求医?她挣扎着起来,去床头柜摸备用药。可是刚下床,她眼前一黑,就栽倒在床边。就这样,她在给丈夫的信中,仍说她和孩子一切都好
“千苦万苦,没有氧气吃最苦;千难万难,在高原上培养孩子最难。”这是阎丽的心里话。
那年,阎丽为了丈夫在高原有个温馨的家,不顾亲友的阻拦,毅然从大城市随他来到素有“万山之祖”之称的帕米尔定居。来到雪山上,强烈的高山反应折磨得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娇嫩美丽的脸蛋也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黑里透红。就在这时,丈夫调到了距离家属区一百公里外的哨卡守防。怎么办?是在这里硬撑下去还是打退堂鼓下山?阎丽心里好不矛盾。面对丈夫渴望的眼神,面对高原官兵的古道热肠,她决心坚持下来跟随丈夫守边关。
一天,被高山病折磨得迷迷糊糊的阎丽不慎打翻了开水瓶,大面积被烫伤,两脚不能走路。正在生闷气的她,得知女儿期末考试仅得了二十七分,不由得又气又恼,劈头盖脸就给了她一顿训斥。女儿委屈得哭了,因为她考的是全班第一名。是啊,在高原上,一则教学质量差,二则因缺氧脑子不好使,能怪女儿什么呢?从此,阎丽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辅导女儿的学习上。尽管如此,女儿的成绩依然是“高原水平”
在“女人村”里,孩子们最盼望和最幸福的时候不是过年,而是守防的爸爸回家。每到运送物资的车队下来,他们都要围着叔叔问:“爸爸什么时候下山?”“女人村”里家家都有鸡,但这鸡平时孩子们吃不着,因为这是迎送爸爸的物品。所以,谁家只要杀鸡,不是爸爸从山上回来了,就是爸爸又要上山了。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任红兵两天水米未进,满嘴说胡话,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了与“牛郎”相会,差点丢了性命
险恶的边防造就了一批勇敢的女性
二十六岁的
军嫂任红兵带着一大包蛋糕、瓜子儿、糖和丈夫最喜欢抽的“雪莲”牌香烟,搭乘一辆军车,冲上了帕米尔高原海拔四千多米的托尔曼索边防连。她要和丈夫一起在山上过年。
途中,他们遇到了可怕的暴风雪,天地间一片混浊。如果停下车来坐等天晴,就有冻死的危险,必须尽快离开这里。驾驶员打开车门下去探路,一股风雪卷进车箱,任红兵冻得缩成一团。她又冷又怕,以为自己要葬身在这“
死亡雪海”里。她终于明白了:一上山,命就交给老天爷了!
强烈的高山反应,使任红兵头疼得抱着脑袋直往车门上撞。将近两天了,任红兵水米未进,嘴里还不停地说胡话。驾驶员吓坏了,他心里清楚:遇到这种天气,十有八九要出事;自己死了事小,如果军嫂“光荣”了,该咋向山里的
战友交代呀!
走走停停,军车在风雪中艰难地蠕动着。零下几十度的天,驾驶员头上却直冒汗。遇到熟悉的“平安”路段,小伙子就拼命踩油门,怎奈雪山上的空气太稀薄了,汽车只“突突”地响,速度硬是加不起来。驾驶着“拖拉机”一样抖动的汽车,小伙子越发着急。
此刻,任红兵的丈夫高立志却急红了眼。他在风雪中不停地抽烟、徘徊。“这到底是咋回事?按说早该到了嘛!”
“连长,快看,灯光!”看到车灯,
士兵们不由得一阵欢呼。
下车时,任红兵已瘫倒了。只见她嘴唇乌紫,脸色蜡黄。夜里,她又发起了高烧,满脸通红。感冒在山上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就会引发高原肺水肿,而这种病抢救的成功概率很低!高立志和士兵们坐立不安。
一夜过去了,任红兵的病在官兵们的忐忑不安中竟奇迹般地好了,士兵们在“生命禁区”里终于见到了一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女性!这决不亚于手榴**淡变成了“飞毛腿”。当连长的丈夫发现,这些日子,尽管巡逻的路线很长,又常遇暴风雪,但连队的士气却格外高。
不久,任红兵悄悄怀上了“帕米尔高原的小种子”,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夫妻俩不得不含泪分手了。
送别那天,全连官兵的眼睛都红红的。尽管任红兵已消失在遥远的群山中,士兵们依然在风雪中拼命地挥手……
也许人们并不了解共和国的边防军嫂,更不了解喀喇昆仑山脚下的“女人村”。且不论军嫂们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能在极度缺氧的高原上生存,并全力支持丈夫守防,“女人村”的“娘子军”已经用鲜血和生命证明了她们是巾帼中的豪杰!

 Post By:2009/5/8 13:32:49
Post By:2009/5/8 13:32:49




 Post By:2009/5/8 18:10:03
Post By:2009/5/8 18:10:03




 Post By:2009/5/9 8:15:29
Post By:2009/5/9 8:15:29


 Post By:2009/5/9 13:35:13
Post By:2009/5/9 13:35:13




 Post By:2009/5/10 9:38:21
Post By:2009/5/10 9:38: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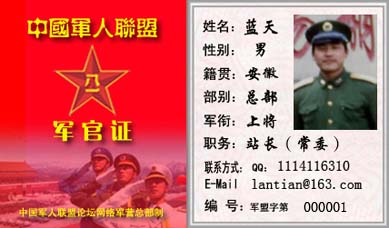


 Post By:2009/5/16 17:01:42
Post By:2009/5/16 17: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