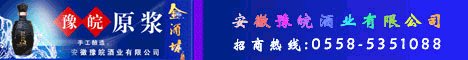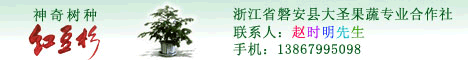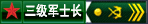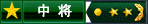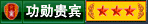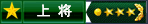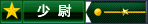冬天里的温暖
文/杜永生
二十四节气已经到了“大雪”。寒峭逼人。水塘里寒森森的薄冰,地面上厚实实的霜雪,纵肆刺骨的朔风,凋零起舞的枯叶,迤扬漫漶的尘埃。其实,这个冬天本身来得就太快。此文最初动笔的时间是在月日,也就是立冬的第四天,温度就骤降下来。每日的平均气温都在度。相比往年来说,这样的变化实在太遽然。立冬之后就是小雪、大雪。难道这个持续寒冷的天气,是空气质量的改善而回归了正常?
周末,我依然回到了老家。天气酽寒,密涌的朔风一个劲地打在脸上,并恣肆地从已经裹紧着的衣领处渗入,虽然是衣取蔽寒,但那丝缕的朔气游离于温热的身体里使人感到了寒噤。
中午,乡下的老同学安排吃饭。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居然在座的还有两位一直在外地打工回来的同学,显然,这样的场景是令人精神激奋的。岁月不饶人,匆遽消逝间。一晃我们都是四十岁的人了,难得有这样的场景,难得能在多年后相遇晤面。那些蕴藏于心际的话语亦如奔腾的河流,倾心相吐。对过往生活的深情眷念,对现今生活的深沉慨叹,无不嵌入在这种浓烈的氛围里。
人生最忆是童年。纵然童年的记忆已经很远,即使那些破碎的片段还留在坚守的阵地,只有这里,才完整地刻录着那段晶莹的岁月,也只有在这里,使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我”,才能在心灵的屏幕上留下一道丰富的折光。
那些温暖的情节莹莹漾漾的打开,心里便有了盈盈满满的情愫。我们几个都是一道上学的,当时都是岁。在他们当中,因为我生日小,算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了。那时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不过开学时的学费却非常低,两本书,就是毛钱。我们的学校,离家也就多米(现在的姚楼)。教室非常简陋,是二大间的土坯房子,一、二两个年级的同学都聚集在这里上课,两根粗大的呈三角形的木架高高地支撑着房子,教室的中间是一堵一米多高的墙体,这就算是隔墙了。由于教室空廓,每到冬天,几扇窗户上的塑料薄膜呼扇呼扇响着不停。那个时候,冬天似乎特别的寒冷,就是这样,我们也并没觉得受不了。主要是对学习的兴趣。
当时惟一的一名教师是村里的朱老师,他一人教两个年级的语文和算术。其实,在寒冷的教室里上课是要经得住承受得了的,对着手不断地呵着气揉搓着,尤其那双脚冻的实在受不了即使不停地跺着,还是像失去了知觉般。我们就等待着下课。只要老师宣布“下课!”你看我们倏地蹿出去。就是为了一些活动,以活动来达到相互取暖的效果。
挤油是当时最热门也是最盛行的活动。几乎一个年级的男生全部参与着。上午一统挤靠在南墙,下午就转移到西墙。一二十个同学开始进行挤油。分成两部分,在墙体的中间划上一道线,谁挤进对方的线就算胜利。那场面热闹的很,鼓劲喝彩声是此起彼伏,高潮迭起。就像现在的“啦啦队”。这些成员基本上是那些身体羸弱的或女同学。当然,女同学越是喧嚷的厉害,我们挤的劲头甭提多高涨了。常常是挤来涌去。浑身大汗淋漓,那还有一点寒冷的感觉啊。说实话,我们当时的穿着忒简朴了,条件好点的是棉衣,不过都是空心的(里面就那么一件薄薄的衬衫或三条襟背心),条件差的就是件不知道穿了多少年、多少个补丁的破棉衣。许多同学没有棉鞋,那么寒冷的天气里还穿着单鞋或呢丝鞋(胶鞋)。
在这项活动中,我要特意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著名的“袁大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拖鼻涕,而且他的鼻涕似乎特别多,总是那种浓浓的、黄黄的、稠稠的。他几乎不去擤过,每到拖曳的长长的时候,要么让它自行坠落,要么用袖口呼啦这么一擦,所以,他的鼻翼两侧以及上衣领子以下和两个袖口上始终有一层明晃晃、白糊糊的干巴物,那就是鼻涕。因为他的劲头大,所以,即使我们一百个不愿意,可是为了胜利,还是禁不住地要拉他入伙。许多时候,我们的肩膀上甚至脸上都留下他珍贵的涕迹。
课间休息时间很短暂。而就是这短暂的时间却是我们在寒冷的教室里和快下课时最大的期盼。经过疯狂的挤油后,有些同学因为燥热就这么大敞着衣服,也很少感冒。有些出汗后用脏兮兮的手在脸颊上这么一抹就成了大花脸。无一例外,我们的衣服上粘满了灰尘和细屑(土坯墙里的黏合物稻草)。这两面墙体米以上的部分却是滑溜溜的,仿佛耕牛来回磨蹭的结果。现在想想,那些土坯堆砌的墙体却是异常地坚固,因其固然,墙体使用数十年都不会坍塌,确实使人惊叹。
女同学们则进行着“斗鸡”的项目。亮莹莹,晶琅琅的笑声,和着沸腾的场景在整个学校的上空萦回往复。简单地游戏过程却给我们带来了不尽的快乐。虽然,结束后我们重新坐在冰冷的凳子上,可内心始终是温暖的。
放学后,我们有时候是不急于回家的。几个家伙相邀来到原野上,找寻那些还没被人刈割的荒草。再玩把火“放冒烟子”。不过大家都是商量好的,轮流带洋火(火柴)。那时,洋火是分钱一盒,可是,也不能始终让一个人从家里偷拿出来。不然是要挨打的。把那些枯黄的荒草点燃,那真叫狼烟四起,烟雾腾腾。我们兴高采烈,手足舞蹈。意为“烤火”。那才是贴近贴身的温暖呢。有的小伙伴们被烟雾熏烘着的小脸红扑扑的,有的眼泪巴泅的,有的止不住的咳嗽。势焰熏天的火焰、浓烈的烟霭能连续多时不散,燃尽了杂草的田野不论是近观或是远瞅,都像一件纯色的衣服缀上了块块的黑色的补丁一样,扎眼、晃目。
还有一次恶作剧。那是在上了二年级的时候。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一帮子又聚集到公场上疯玩着,因为那天特别寒冷,再怎么疯玩,似乎身上都没有热度。不知是谁提议,去烧草堆子。因为我家离公场最近了,所以,取“洋火”的任务就是我了。我劲杲杲兴冲冲地奔回家,乘父母没注意,赶紧从锅洞子里摸出一盒刚用了几根的洋火,又跑回去。我们就聚拢在草堆子旁,看着把火点着。你想想,当时还在刮着大风呢,这些都是干生生的稻草,一点呼啦就着开了。没想到,因为火借风势,把处在下风头的一个伙伴的头发也撩起来了,不仅头发烧的一塌糊涂,连眉毛都焦黄焦黄的。整个一个黑脸。看来火是控制不住了,我们都感到非常害怕,不知谁先喊了声“赶紧跑!”,你看大家一个个像惊猿脱兔似的奔回了家。这个草堆子不大,而且是单独设立的,要是像另外一边连成一片的话,那真的就是闯了大祸了。就是这样,我们回家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我记得最惨的是道胜,他被父亲抽了几耳光还罚跪在破碗茬子上。我呢,也是被父亲狠很地打了一顿。
当时我们上学是有强烈地时间观念,生怕起来晚了而迟到。所以,常常在天刚蒙蒙亮就随着母亲起床了。当母亲把米淘好水添上锅盖合上时,我便积极地坐在锅地上,烧锅。那仄小的空间,那熊熊的火焰,身上总是热烘烘的,甚至都舍不得离开锅地。有时候时间紧张了,来不及吃早饭,就随手拿起一个烀熟了的滚烫的山芋,拿在手上左右交替着,既暖手,也暖心。快到学校了,掰开,狼吞虎咽,有时阗噎的喘不过气来。晚上做作业时,母亲总会把煤炉打开,把我们穿了一整天有些潮湿的鞋子、袜子和鞋垫子统统烘烤着,这样我们早上起床穿在脚上就是温暖的感觉。
后来我们在三年级的第一学期后,全部搬到了乡中心小学上课。因为中心小学的所有教室都是砖头墙体,对于那些挤油的活动就再也没法进行下去了。不过,诸如“放冒烟子”,烧树叶子还是继续着。
往事的排浪阵阵、涌涌袭来。数年后能与当年的伙伴们相逢,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一件快事,我们的记忆犹新,我们的娓娓道来,嘴角都会挂着甜蜜而会心的微笑。离童年愈远,离童心愈近。其实,我们生命的成长就是一处处的驿站。每一处地方,都会引起我们牵筋扯肉的追溯与愐想。在那每一处驿站,都曾经历过过艰辛与磨难,也体验着温暖和欢乐。就像这些融和着我们童年快乐而简单的活动,却给我们在寒冷的冬天里带来了持久的温暖。它给我们的是一种深明的感动,是一种精神的契合和心灵的体贴,如同“血液、脉动”始终潆洄在心田。只要我们一闭眼睛,它们都能幻化成幸福、温暖的回忆。(全文个字,于年月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9 8:25:19编辑过]

 Post By:2009/1/19 8:23:32
Post By:2009/1/19 8:23:32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Post By:2009/1/19 14:18:04
Post By:2009/1/19 14:18:04




 Post By:2009/1/19 15:52:25
Post By:2009/1/19 15:52:25


 Post By:2009/1/19 20:29:31
Post By:2009/1/19 20:29:31




 Post By:2009/1/20 10:34:51
Post By:2009/1/20 10:34:51




 Post By:2009/1/20 18:32:43
Post By:2009/1/20 18:32:43





 Post By:2009/1/20 21:30:50
Post By:2009/1/20 21:30:50




 Post By:2009/1/20 23:51:33
Post By:2009/1/20 23:5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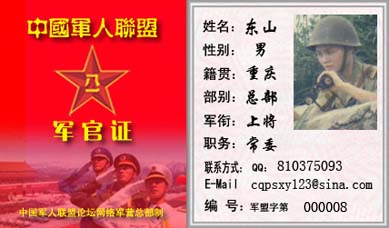


 Post By:2009/1/23 10:46:14
Post By:2009/1/23 10:46:14


 Post By:2010/7/17 17:19:59
Post By:2010/7/17 17:19:59